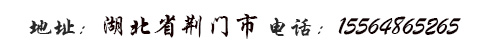灰白色的寂静
|
治疗痤疮北京医院 https://m-mip.39.net/czk/mipso_8595980.html 窗外赵定河 灰白色的寂静 ●芭蕉雨声 五点窗外的霾一直持续到现在,八点了,鸟儿们一声不吭,飞影也没有一个。单纯的灰白色背景里,窗外的楝树站出了平时没有的气质。用笔在玻璃上可轻易描摹出枝丫和楝豆的细节。 赵定河沉寂。 人和狗都没有出来,灰蒙蒙分不出天和地,河流忽然不见,时间凝固,整个人世一片痴。 出不得门,只在屋内周旋。 水养的紫色鸭跖草又开出一朵小花,明明灭灭在一个梢头数不清崩开过多少朵,开败结子,也不耽搁再萌花蕾。钟情它叶子的颜色,紫得发蓝,很深沉的色泽。天性里我对明艳的东西不热,老色儿耐看,红就红得浓郁,大量加水稀释才能蘸出一些儿胭脂粉。蓝也蓝成黑色,阳光下洇出幽幽的蓝头儿就好。对颜色和光影的感觉源自骨子里,后天很难偏转。 坐在雾霾围拢的窗下,拾掇前天从老家带回来的皂荚。荚果外壳的紫棕色深得发黑,近乎黑紫。果仁棕红,滚圆有质感。老家后院这棵皂角树,以前不设意它结果的事,今年结得可稠,遍地都是落荚,东屋屋顶上躺了一层,堂屋房顶也有,东邻荒芜的院里也是。没住人,也没人在意,我遇着宝贝样拾了一大兜。 老家大门,我在这儿出生,长大,门前有个大水池,现在还有。 村里路面修整硬化,一直通到家家户户的门口,我可以踩高跟鞋回娘家了。原先想着水泥路不如石子小道意境好,铺好后看着挺舒服,村子换上新衣裳似的精神多了,亲人们走路方便,这个最要紧。 老大娘三周年祭,事儿上见到了我昔日伙伴,大娘娘家人里有一个是我初中同学,我都记不得她的名字了,她看着我笑。小英的手还是冻得红肿,摸着冰冰凉。紧身棉袄也太紧了,穿个宽松的还暖和些,袖子也短,怕冷还不盖住手背。她说是胳膊长得太长,没法儿。她细高条儿,高中之前没有我高,猛一窜,我再没撵上她。我让她来找我玩,她说新乡太远,走不到。还打麻将?不,抹牌。小英抹那种很古老的长条形纸牌,我奶奶活着时最得意玩儿这个,玩了一辈子,不曾想现在还有这种牌卖,还在玩。小英说可简单,起九张,也是饼,条,万。我印象中厚墩墩的一摞,图案复杂,神神秘秘不好记。我一直惦着小英,心里和她亲,可很难相见,见了也是匆匆别开。 老皂角树。 我到家就不想走,弟妹催促,金凤陪我我摸摸这儿看看那儿,指指点点,每一处都有故事,故事里的我们都正年少。房屋虽说是嫂子弟妹的家产,但她们对这儿的感情远不如我们的深,这是我和妹妹永远舍不下的家。 家里空落落的。终究都顺着平坦坦的路又下山出村,奔城里来了。我把村的寂静和单纯又还了回去。 呆在雾锁的城里想象老家的样子,石头垒的小院,小院旁的酸枣树柿子树应是猫一般温顺,房后的山坡跟我窗外的河一样隐匿不见,只露出简约的筋骨。皂角树仍在村的核心位置站定,隔着几重阻碍我只需遥遥一望,甚至一个低头,都能把它看得真真儿的。不管是在浇花还是择菜时候。 想起二姑的话,她摸着自己的头发说都白完了,灰白灰白。我们这些老侄女笑她矫情。她凑到我脸上使劲端详,得出一个结论,说,不中了,也不中了。惹人大笑。如花似玉的姑娘都去哪儿了?我有一个长不大的姑姑,很可爱。 灰白色天宇下一直都藏着最原始的天真,如同笑生双颊而白发苍苍。时光走到哪一天,不改的是干干净净的幼稚心。不中也中了。 年1月12日农历腊月初七星期六重度污染橙色预警。 老堂屋,奶奶以前住这儿,门前都是花儿,大丽花最好看。 这个高高的小道,妹妹们说,以前骑车出出溜溜来回跑。 刚下车,嚷嚷着拍照拍照。 手里拎满满一兜皂荚果。 左上岸头上是麦场,现在小队房里住了人家。 金凤锁大门。门头匾额是二伯父获得的荣誉。 芭蕉雨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uyazaoa.com/zyzxt/7239.html
- 上一篇文章: 民间中医实用技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 下一篇文章: 陈起江湖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