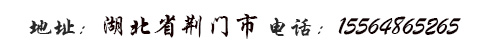红脂块块香
|
西风紧,气温骤降。 上周末驱车驰上阳澄湖美人腿, 买回十只生龙活虎的大闸蟹, 没过一个星期就被我一人独食完毕。 五对大闸蟹歼灭了, 窗台上半开的秋菊也怒放了。 菊黄蟹肥,心满意足, 想起贾宝玉说,“指上沾腥洗尚香”, 不知道敲打完这篇有关大闸蟹的文字后, 键盘上会否留有余香…… ?????? 小时候去外婆家,如果是这种秋冬季节,外婆家墙上就会贴了好多白翅膀的“小蝴蝶”,其实,“小蝴蝶”是大闸蟹的两只绒螯掰下来做成的,湿漉漉的时候摆好造型摁到墙上,就黏住了,来年黄梅天之前,一般都不会掉下来。 吃螃蟹在那时的苏州不算奢侈消费,母亲和外婆都喜食,小蟹面拖,大蟹清蒸,从八、九月吃到冬至前,除了叮嘱孩子吃完要喝一杯姜汤,并且同日不可吃柿子,其他便不再有什么禁忌。 挑蟹、洗蟹、蒸蟹、剥蟹、食蟹,最后洗手,享用螃蟹的过程是冗长而繁琐的,着实需要些耐心,因此,女人天生是吃螃蟹的专家,不仅吃得细致,而且吃得文雅,还可能吃出些行为艺术来。 螃蟹性寒,林黛玉体弱,只吃了一点肉,便找合欢花浸过的烧酒来驱寒,自然意犹未尽,便随口吟诗道: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古来那么多写螃蟹的文字,我独记住了这“红脂块块香”,每回剥蟹,对着那蟹黄蟹膏下口咬时,都会再一次地崇拜林黛玉,真的是“红脂块块香”啊。 淡水蟹中,湖蟹最上品,河蟹、江蟹次之,溪蟹、塘蟹再次之。苏州阳澄湖的螃蟹,人称大闸蟹,是湖蟹中最好的品种,没有之一。据说因为阳澄湖底是坚硬的石头,螃蟹在湖底横行,炼出了紧实的肌肉,加上水质十分适宜螃蟹生长,因此,阳澄湖蟹肉质肥美鲜甜,不用蘸料,才正好品尝。 “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这是民国才女汤国梨对阳澄湖蟹的痴迷,她本浙江人氏,跟随丈夫章太炎旅居苏州,此后年年不忘,最终选择苏州为长居地,一直住到了九十七岁高龄去世。 上海人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坚定拥趸者,民国著名女星胡蝶自幼生长在上海,她一口气能吃七八只蟹,而且吃法高明,动作娴熟,在明星电影公司有“食蟹拥趸”的雅号。胡蝶晚年侨居加拿大,有朋友去探望时问她:“你最忘不了上海的是什么?”胡蝶笑答:“大闸蟹!” 如今,上海人年年不忘来苏州吃蟹,顺便一家人出来秋游。相城区美人腿是阳澄湖蟹重要的交易区,也是沿湖农家乐的集中地。双休日的中午,扎堆的农家乐门前停满了上海牌照的汽车,男女老少全家出动吃大闸蟹来了,吃完,再买些带回去,有些上海的老阿姨挑蟹,比苏州人眼睛还尖。 正宗的阳澄湖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看起来孔武有力。首先,阳澄湖蟹的背壳平滑有光泽,既不似巢湖蟹的黄灰,也不若崇明蟹的黑灰,而是灰中泛青,透着明亮,人称“蟹壳青”;再将螃蟹翻身看肚子,阳澄湖蟹的脐腹晶莹洁白,白中带青,有光泽,这是因为湖底长有茂密的猪鬃草,螃蟹常在水草上爬行,将自己的肚子蹭的锃亮,显然,普通湖蟹米白色的肚子,或者污泥斑斑,或者混浊黯淡,是无法蒙混过关的;再者,看蟹脚,阳澄湖蟹的脚爪不像一般蟹爪的灰褐色,透过阳光观察,它的脚爪居然呈金色,包括两只大螯,上面的茸毛也都是金黄色的,将它抓起时,金戈当剑,颇有将军威仪,放入蟹池,又极有突围本领,一不留神就从滑溜溜的四壁爬出,甚至连玻璃壁都奈他何。 往年,美人腿沿路都是叫卖的蟹农,今年道路两边正在修整植被,蟹农们被统一安排到了旁支的道路上,一律红色的遮阳棚,统一的蟹池,单边编号排列,一百几十家售蟹的棚子绵延数里,望不到头。 看了几家,问了几家,蟹农都极友善,不买也没关系,还是笑嘻嘻的,若是隔壁棚子里的阿姨做成了生意,还帮着一起扎蟹。 所谓扎蟹,是将大闸蟹的两螯八脚蜷起来,用棉纱绳子十字形捆好,如此,就解决了像我这样对螃蟹又爱又怕的吃货之大问题。 记得小时候父母买回来的大闸蟹都是张牙舞爪的,并不捆扎,洗蟹时,须用手自蟹背一面抓住背壳,两只大钳子虽然疯狂舞动,却怎么也钳不到抓它的人,但稍不留神,刷它肚子的板刷却被它死死钳住。这样的螃蟹,我是害怕的,他们强壮到下了锅之后会把木质的锅盖顶开,每每这时,母亲都拿几个秤砣过来压上,才勉强镇住,随着锅里沸水的咕噜声渐响,蟹爪的躁动声渐渐也停了。 其实那个时候会有些不忍心,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才是最凶猛的动物,即便柔弱如林黛玉这样的女孩子,看到盘中通红透亮的螃蟹,也不觉它面目狰狞,轻车熟路,掰腿剥壳,依次食之。 食蟹,可蒸可煮,但蒸的或许更鲜嫩好吃些。为了驱寒,蒸螃蟹时要放生姜和紫苏,没有紫苏的话只生姜也行。蘸料用香醋,加点白糖,切姜末放在一起,略加一点热开水化开白糖,搅拌均匀。很多饭店的姜醋不加糖,不是苏州人的吃法,我不喜欢。 先吃蟹坨坨,还是先吃双螯与腿,其实都是个人习惯。我喜欢先吃腿,因为蟹坨坨太烫。吃完八条蟹腿,然后吃蟹坨坨,最后将双螯内的肉仔细剔出来,放在蟹斗中,浇上姜醋,大快朵颐。 重点说蟹坨坨,这也是吃货们最心驰神往的所在。 所谓六月黄,乃幼蟹,没什么肉。食蟹必定要等到九月,才可以开始。倘再等一等,等到“西风起,蟹脚痒,九月圆脐十月尖”,食蟹的黄金季节才真正到来。 圆脐是指雌蟹,尖脐是指雄蟹,也就是说,农历九月吃雌蟹,蟹黄满、肉厚;农历十月吃雄蟹,蟹膏足、肉坚。深秋初冬,雌蟹雄蟹一概黄膏肥美,只管享用,无问西东。 闷头吃大闸蟹的时候,两手不得闲,且湿哒哒腥香交织,正忙得不亦乐乎呢,冷不防哪位仁兄端着酒杯过来敬酒,此种尴尬,是食蟹经历中最不好的体验。 闷头吃大闸蟹的时候,最好也别跟我说话,我不爱使用工具,全凭铁齿铜牙应对,还得时时提防蟹螯蟹腿儿上的尖厉,一分心,戳破嘴皮的事就会悲惨发生。 美食当前,共享有共享的欢乐,独享有独享的趣道。 《红楼梦》中写的大观园螃蟹宴十分生动热闹,且可以看出,螃蟹在那时虽为美味,但算不得珍馐,一场欢宴,主仆同食,其乐融融,甚至丫鬟们拿蟹黄抹对方的脸取乐,如同今天我们把蛋糕上的奶油抹到彼此脸上,读到此,恨不能大喝一声“住手”。 如今我们面对阳澄湖蟹,肯定每一只都要吃得干干净净方才罢休。正因如此,食蟹,也许更适合私密的空间,独享,或只二三至亲,围坐剥蟹,不适合敷衍聊天,更不适合互相敬酒攀谈。 快节奏的社会不仅压缩了我们与食物相处的时间,也扭曲了与之面对的空间。当我们一边握着手机刷屏,一边心不在焉地吞食,对于供养人类的自然界的食物,我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尊重。 食蟹,让人与食物相处的节奏慢下来,这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在人们对食物渐失感恩的今天,品尝的专注,成为我们唯一还可以,也应该去做的事。认真的吃,慢慢的吃,细细的吃,也许,只有食蟹的时光里,我们才恢复了对食物最本源的敬畏。 所以,很多男人声称不爱食蟹,不是不喜美味,是未尝静心。是的,贾宝玉还说了,“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枉他还有袭人专门剥了蟹肉蟹黄放在蟹斗里伺候他吃,还嫌忙不过来,今天于这浮躁的世间,很多嫌麻烦的男人就只好选择放弃了。倘若胡乱嚼了,不仅暴殄天物,而且还被苏州人戏称为“牛吃蟹”。 好吧,说的不是所有男人。其实男人中喜欢食蟹的也不在少数,说几个奇葩级别的吧。 清代美食家张岱算是最会吃螃蟹的一个男人,每到十月,与友人组成“蟹会”,一人分六只蟹,为怕冷腥,便轮番煮吃,还辅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等佳肴,餐后漱口也颇讲究,用的是兰雪茶。张岱在他的《食蟹》一文中写道,“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无他,乃蟹。” 明代剧作家李渔嗜蟹如命,自螃蟹上市之日起到断市之时终,他家七七四十九只大缸里始终装满螃蟹,用鸡蛋白饲养催肥。他无一日不食螃蟹,因担心季节一过难以为继,还要用绍兴花雕酒来腌制醉蟹,留待冬天食用。在没有螃蟹的季节,李渔先取瓮中醉蟹过瘾,而后腌蟹的酒也不会浪费,称为“蟹酿”,一直喝到来年螃蟹上市。 莫以为贪食螃蟹的都是古人,今人也当仁不让。围棋大师聂卫平有一次去香港,在金庸家中作客,金庸设蟹宴招待。聂卫平一口气吃掉了13只大闸蟹,四座皆惊为神人。 有人痴迷食蟹,也有人执着于探究蟹文化。之所以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实在是热衷于此的文化人太多。就说阳澄湖的螃蟹为何要叫大闸蟹吧,文人们也研究得乐此不疲。答案至今有几种,彼此各有千秋,也各不相让。 最简单的一种说法,是捕蟹时用草闸,故称闸蟹,个头大,称为大闸蟹。 第二种说法与前者相似,但形象生动得多,“凡捕蟹者,他们在港湾间,必设一闸,以竹编成。夜来隔闸,置一灯火,蟹见火光,即爬上竹闸,即在闸上一一捕之,甚为便捷,之是闸蟹之名所由来了。”这段文字见诸现代作家包笑天晚年所著的《大闸蟹史考》。 第三种说法,与第二种有点近似,但似乎更注重大闸蟹之名号的光荣与梦想。螃蟹在洄游产卵的过程中,须经过一道道拦水堵潮的闸门,而能爬过那沿路大闸的蟹,必定身强力壮,这样强壮的蟹才是好蟹,这样的好蟹才能被叫做大闸蟹。 第四种说法,则完全来自大闸蟹的读音。“大闸蟹”,原本应为“大煠蟹”。“煠”,与“闸”同音,在吴方言中是水煮的意思。加水“煠一煠”,就是加水“煮一煮”,且并不放油盐,是清水煮,比如煮白煮蛋,苏州人叫做“煠白焐蛋”,清水煮蟹,就被叫做了“煠蟹”,所以有时也讲“清水大闸蟹”,确切地说,大闸蟹指的是用水煮的烹饪方法端上桌的螃蟹。 那么,但凡清水煠的蟹就是大闸蟹了吗?我却觉得这个称呼其实隐藏了一种身份认同的含义,如果这蟹足够大、足够好,一定足够美味,可以当得起张岱所言的“不加盐醋而五味全”,才配叫做大闸蟹,倘若品种不济,或者身量不足,用来做成醉蟹,或者切成两半面拖、油炒,就不是所谓的大闸蟹了。不过,面拖蟹也是极好吃的,或者加了毛豆子的螃蟹炒年糕,亦是人间美味。至于蟹粉面、蟹粉小笼包、蟹粉小馄饨、蟹粉豆腐等,又是吃货届的另一场味蕾盛宴。 吃大闸蟹说到底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前螃蟹不贵,不用有钱,但要有闲,如今大闸蟹身价不菲,那可真是要有钱有闲才吃得了。 剥蟹是个技术活儿。记得小时候,我是不吃蟹腿蟹钳子的,只吃完蟹坨坨里的蟹黄蟹膏就满足了。姐姐很有耐心,她会将蟹肉一丝丝的细致地剔到蟹斗里,倒上姜醋后给我吃,我也觉得这一口吞的感觉颇为爽利,直到长大后才明白薛姨妈的那句话,“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 我家有剥蟹的工具,但我从不用,也许是用不习惯,也许是心里对工具有抵触。在我看来,手抓羊肉就是应该用手抓,而大闸蟹,就是得用手指掰,用牙咬,用唇和舌尖第一时间感觉那道鲜美。有时心想,等哪天老到用牙咬不动再说吧,母亲八十岁以前吃蟹也从不用工具,一样吃的有滋有味,干净利落,我相信我也能。 煠一次螃蟹,厨房里腥味几日不散,我觉着是余香,我先生觉得不堪忍受。很多食物都可能遭遇这样的尴尬,如榴莲,如香椿,如臭豆腐……凡此种种,我都觉甚香。不过,吃完螃蟹洗手还是有必要的,虽然没有大观园里用的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但用茶叶水洗一洗,也可免去许多尴尬。 这篇文章应该有个轻松的结尾,于是想到一件有趣的小事:有一年家里吃蟹,第二天放学的时候,老师把早晨我们交上去的作业本发下来,发到我,老师神秘地笑了一笑,轻声对我说,昨天,你吃大闸蟹啦?!我打开发下来的作业本,果然,腥风袭来,蟹天蟹地。 (创作于年11月) 链接 蟹八件蟹八件,是苏沪杭一带民间流传、专门用来吃蟹的工具,是明代一个叫漕书的人发明的,当时仅仅只有锤、刀、钳三件工具。 之后,蟹四件、蟹六件、蟹八件,甚至蟹十件、十二件等,都是在蟹三件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起来的。 最常见的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蟹八件,包括小方桌、腰圆锤、长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钎子、小匙,分别有垫、敲、劈、叉、剪、夹、剔、盛等多种功能。 蟹八件多由铜器制成,讲究的大户人家则会选用白银制作。晚清到民国时期,蟹八件作为精美的工艺品成为苏州姑娘的嫁妆之一。 吴迈赞赏 人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ingbeimum.com/zyzls/2073.html
- 上一篇文章: 差点害死李未央的问荆草
- 下一篇文章: 临沂人的福利来啦蟹都汇蟹谢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