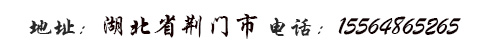华化离散与治理ldquo华人穆斯林
|
中科大型白癜风公益援助 http://m.39.net/pf/a_4892467.html 华化、离散与治理:“华人穆斯林”与“一带一路”的前现代关联 张云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广州) 摘要:“华人穆斯林”形成于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东亚大陆进行文明对话的历史社会实践中,是一个兼具华人背景、伊斯兰信仰和本土化特征的多样性跨国族群。在前现代时期,“华人穆斯林”通过在东亚大陆的迁徙、流动和繁衍把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连结起来,形成了以中国为枢纽、联通海陆的“一带一路”网络。“华人穆斯林”华化、离散和治理的历史是“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的前现代历史叙事之一,他们既是“一带一路”早期的开拓者,也是“一带一路”遗产的天然传承者。从前现代的历史路径来阐释“华人穆斯林”与“一带一路”的关联性,对于挖掘“一带一路”历史遗产,建构一个多元现代文明国家有重要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华人穆斯林”网络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一种跨国治理的方式。把“华人穆斯林”作为一种理解“一带一路”的视角和方法,有利于中华文明和中国经验在“一带一路”上的社会化,在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挖掘独特的东亚历史经验,建构一种包容性的区域或跨区域治理模式。 关键词:华人穆斯林;华化;“一带一路”;前现代 一、研究缘起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跨国移民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常态现象。“华人穆斯林”是一个兼具华人背景、伊斯兰信仰和本土化特征等多重身份的多样性跨国族群,是目前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与宗教学等学科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1)近代以来由于族群关系的演变和学术话语权中的“民族国家”倾向,华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也处于嬗变当中,通常是文明或宗教范式主导了相关研究。(2)目前,“华人穆斯林”(3)在国内学术界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相关研究也颇具挑战性: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界互动增多,中国学界秉持的“多元一体”的中国叙事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文明冲突论”的冲击;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民族国家”情结则受到“华人穆斯林”二元身份的挑战,既有的关于民族的概念、叙事和范式越来越难以回应多元化、碎片化和本土化“身份政治”(IdentityPolitics)的诉求(4)。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华人穆斯林”触及的正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叠合的“身份政治”问题,其中,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挑战,亟需通过务实和理性的学术态度加以正视并进行研究。 自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研究成为讨论的热点,学界通常侧重于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的分析,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族群政治、宗教差异与文化冲突的研究并不深入,“华人穆斯林”与“一带一路”的关联性研究则几乎是缺席的。(5)实际上,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穆斯林世界有重要的前现代关联,(6)“一带一路”战略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穆斯林世界相关国家的关系走向。“华人穆斯林”的“身份政治”,是“一带一路”叙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7)本文拟把“华人穆斯林”作为一种理解“一带一路”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历史主义”的前现代路径追溯“一带一路”的社会文化生态,对现实主义权力话语主导学术机制的现状进行回应,推动形成以“华人穆斯林”为切入的文化融合与协调机制。 二、“华人穆斯林”的概念辨析与现状特征 “华人”不只是一种祖籍东亚大陆的族群的自然人身份,也是一种传承中华文明的社会人身份,“华人”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8)具备华人主要特征的族群大多是东亚大陆上的“原住民族群”(Indigenousethnicgroups),也有从海上或陆上迁徙而至的外来族群。中华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融合了儒释道等不同文化,与伊斯兰、基督教等宗教文化兼容并蓄。按信仰划分,华人可分为华人佛教徒、华人穆斯林、华人基督徒、华人民间宗教信徒等多样性群体。(9)其中,今天国际学界所说的“华人穆斯林”在东亚大陆有上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该群体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长期对话的社会实践中实现了本土化,其二元特征最为明显,宗教性最强,其“华人性”(Chineseness)也尤为值得探讨。 本土语境下的华人与穆斯林的融合经过了一个伴随时代而流变的过程,东亚大陆是最主要的本土化场域。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语境,中国境内伊斯兰信徒有蕃客、回回、回教徒、回民、回族等的不同称呼,都是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形成的,不同的称呼体现的是不同的身份认同。“蕃客”在历史上是一个外来族群客居中国的概念,从字面意思上看,穆斯林仍是“化外人”的法律身份,作为中国本土居民的资格还没有得到承认。“回回遍天下”的局面是在元朝时开始形成的,这时的回回是中原人对西域族群的泛称,其中包含了信仰摩尼教等其他宗教的人。实际上,回回并不全是穆斯林,而是作为当时的色目人的一种。根据元朝的“军户”制度,回回人“随地入社,与编民”[1],可见回回已经逐渐本土化,并被当作臣民看待。元明以来,“回回”逐渐成为一个融合汉、蒙等多个族群的新的民族共同体。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亚洲国际关系的变局深刻影响了中国境内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在反对满清的统治中,中国境内的不同历史族群开始向现代“民族”转型,在臣民、回民和国民身份的三重变奏中,“回族”的叫法逐渐开始流行。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试图“回化”的国民身份(即回民)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通过民族识别完成了公民身份的转变,作为少数民族的身份也在宪法中确定下来,回族的概念和称呼也一直沿用至今。“‘回族’作为新的族属称谓与范畴,在国家内部机制的运作下,基本上已将这种游移在传统‘非夷即夏’间的适应矛盾予以化解。”(10)然而,这种源于苏联的民族划分也带来了问题,如蒙回、藏回、白回、苗回、萨拉回……的出现,如果把回回作为穆斯林的统称,中国西北地区阿尔泰语系的穆斯林并没有涵盖其中,东南亚的华人则又把“回教”“回教徒”的指代范围扩大到当地的马来穆斯林中。(11)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跨越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多样性族群,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概念和称呼,都需要重新审视。本文把“华人穆斯林”作为一个更高一阶的文化人类学概念,来指代融合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二元/多元合一的多样性族群。 “华人穆斯林”是指那些有中华文化背景、与中国境内族群有血缘关系的伊斯兰信徒,其身份基本上属于华人,伊斯兰信仰是与其他华人族群最大的不同。国际学界有ChineseMuslims、MuslimChinese、Sino-Muslim、China’sMuslimNationality等的叫法,分别翻译为“华人穆斯林”“穆斯林华人”“华夏穆斯林”等,可以统称为“华人穆斯林”,(12)以与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相区分,东南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华人族群,通常使用这一概念,如“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协会”的叫法。在国内学界,这个概念最早由曾留学马来西亚的回族学者刘宝军提出,在年的一本著作中,他把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放在一起,用于指代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有穆斯林信仰的海外华人。在刘宝军的分类里,“海外回族”是指移民海外之前已经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汉语穆斯林(在中国被称为“回族”),“华人穆斯林”则是指那些移民海外的华人在现居国接受伊斯兰信仰的群体。(13)刘宝军的分类是基于海内外信仰伊斯兰教的不同华人群体之间相对封闭的状况。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种把海外回族与华人穆斯林相区别的分类已经与华人穆斯林的现状相脱节,这种分类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化”的民族划分也不一致。在笔者看来,“华人穆斯林”可以作为信仰伊斯兰教且与中国有亲缘关系的不同华人族群的统称。理由有三: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传播技术和资讯的发达已经打破了不同的华人穆斯林社群间相对封闭的状态,不同年代皈依伊斯兰的华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华人穆斯林的称呼成了海内外华人伊斯兰信徒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单一少数族群如潘泰人(Panthay)的称呼,导致其作为移居国的少数族裔越来越孤立,不利于社会交往和身份认定。(14)其次,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融入世界速度加快,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华人”逐渐成为与中国有亲缘关系的穆斯林在社交时可以标示的重要身份之一。再次,穆斯林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现代宪政的发展使华人穆斯林已经拥有合法的国民身份,华人穆斯林在不同国家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状况大大改善,华人、穆斯林和移居国国民的多元身份日益在本土化中得到妥善处理。尽管这一概念没有被国内知识界广泛使用,但在华人和穆斯林的跨文化流动中,有华人背景的穆斯林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汉语穆斯林(通常是指回族)的历史与文化视为一种共同的“母体想象”,并试图将他们的“离散想象”(diasporicimagination)与海外的伊斯兰文化与传统相结合。今天,即便在欧洲,越来越多原籍中国的穆斯林也开始有意识地突出自己与中国的关联,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他们更愿意通过强调其华人身份来凸显其中国背景。[2]总体上看,“华人穆斯林”的身份越来越被这个信仰伊斯兰教但文化上植根于中国的群体所认可,同时在穆斯林世界和华人社会,这个群体也逐渐被接纳。(15) “华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是跨文化的,是在本土化过程不断调试形成的。这种文化认同既是基于儒学伦理的,也是基于伊斯兰信仰的。首先,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儒学伦理可以作为宗教性伦理即“儒教”伦理与其他宗教进行类比研究,与其他宗教在社会实践中也有共性,如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亚洲价值观”的理论探讨与社会实践,就融入了儒教与伊斯兰教的共享性文化。(16)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儒教已经在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居于中心位置,“儒法天下”的政权模式也被奉为正统国家的治理之道,儒家伦理自然成为伊斯兰教教诲不可缺少的部分,渗入到作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的道德和信仰生活中,这种儒学观念在穆斯林“华化”后自然也得到了传承。其次,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表明,伊斯兰教的传播是一个“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过程,中亚、南亚及东南亚乃至欧美的穆斯林与伊斯兰教兴起之地的穆斯林有明显的不同。(17)穆斯林本土化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地方性的过程,包括地方地理和社会环境的文化调适,以及本土认同的形成”,是一个“积极参与和创造的”过程。[3]华人穆斯林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穆斯林,是一个脱胎于中华文化母体的复杂而又多样的族群,经过了一个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的“华化”过程。“回族清真寺的建筑物表面上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但是表达的是伊斯兰教义,用儒道思想阐释伊斯兰……石雕、木雕、香炉等都明显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但皆已被调适,以此表达穆斯林的象征和认同,是很有意义的本土化。”[4] 从文化和语言特征看,穆斯林在中国经过了上千年的“本土化”社会实践,其文化想象和信仰归属已经超越了祖籍何地的血缘追问,反而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出生地的血缘、亲缘和族缘关系成为其文化想象的母体(18),以回回为代表的“华人穆斯林”形成一种逆向辐射,以中国西北为中心,以汉语为第一语言,向南部和西部延伸,并影响了马来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与中国有渊源关系的穆斯林。(19)如今,尽管华人穆斯林母语为其他语种的现象普遍存在,但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通常是最主要的使用语言。按照语言划分,华人穆斯林有原生汉语穆斯林(bornHan-speakingMuslim)、阿尔泰语系穆斯林、马来语穆斯林及其他语系的穆斯林,尽管第一语言大多不同,但普通话通常是华人穆斯林的共同语言。语言文字是族群身份的关键标示,是否使用汉字和普通话,也成为判断其“华人穆斯林”身份的最重要标识之一。 从地域分布来看,今天的华人穆斯林以中国为主体,向中国周边的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国家延伸。国际人类学界在研究“华人穆斯林”时,通常将其视为一个“去国家”的族群概念,故中国本土的穆斯林通常也涵盖其中,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以及苗回、蒙回、藏回、傣回等少数民族乃至汉族中的穆斯林。境外的华人穆斯林,主要分布在东亚大陆与中亚、东南亚、南亚接壤的地带,如中亚的东干人(Tungani)、缅甸潘泰人、泰国北部秦和人(Cin-Ho)等。西亚北非也有部分华人穆斯林,但其除了保留华人文化的部分特征,当地文化色彩明显偏重,欧美的华人穆斯林大多是通过留学、经贸等迁徙和繁衍而来。 三、“华人穆斯林”的“华化”、离散与治理 穆斯林的“华化”起源于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以来阿拉伯世界向东的商贸、宣教和传播的过程。在伊斯兰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鼓励下,伊斯兰教通过海路和陆路(即“一带一路”)传入东亚,来自西亚、中亚的穆斯林在中国历史叙事中的“南洋”和“西域”一带通过战争、商贸和通婚等方式与东亚的原住民互动,阿拉伯人、突厥人和波斯人等穆斯林族群与东亚大陆的蒙古人、契丹人和汉人等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一个兼具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华人穆斯林”群体。 在前现代时期,并不存在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意义上的冲突,更多的是恩格斯所说的野蛮与文明之争(20),东亚大陆则表现为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其他族群二元结构的“华夷之辨”。“中国的统治者并不像欧洲的基督教君主那样担心异端宗教的存在。其他宗教学说只要不被视为煽动叛乱的根源,就能被统治者所容忍而在中国社会获得立足之处。在中华帝国,多种信仰能够并存并且在多方面展开竞争,这跟欧洲的情形大不相同。”[5]在关于“一带一路”的典籍中,不管是阿拉伯传记还是汉语文本,宗教冲突一直不是历史叙事的主线,不同物种、货物、族群与宗教的互动并最终向更高阶的文明圈流动才是历史的主流,中原、边疆互动的二元“内旋型”区域治理一直是东亚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特征。(21)一方面,在陆路上,中亚诸游牧民族与中国北方诸民族长期拉锯互动并逐渐本土化(陈垣称其为“华化”),在中国西北边疆“屯聚牧养”;另一方面,在沿海地带,西亚商人从印度洋沿岸出发经南中国海到中国东南沿岸从事贸易,唐宋以来逐渐在东亚南部沿海地带落地生根。经元明两代,本土化的汉语穆斯林在东亚已经形成,汉语叙事中称其为“回回”(22),周边的穆斯林族群在政治上也大体接受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原-边疆”互动的宗藩体系,文化上也受其影响。 元朝是“华人穆斯林”在中国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由于蒙古的西征,西亚和中亚既有的穆斯林世界秩序遭到破坏。“西征使回回人大批东来,壮大了伊斯兰在东方的力量,也加强了我国和中亚、西亚伊斯兰世界的联系。”[6]根据民国学者陈垣的考证,元朝是西域人的“华化”时期,(23)蒙古学学者约翰·埃尔弗斯克(JohanElverskog)认为“在后蒙元的政治分裂和宗教整合期间,在中国西北部形成一个庞大的华人穆斯林社群……在西到莫卧儿、东到中土、北到蒙古、南到西藏的不同区域间发挥了重要的枢纽功能。事实上,华人穆斯林充分利用其中国与伊斯兰的复合身份,横跨中土、蒙古和西藏,并确立了自己在不同环境中的商业地位。”[7]他们连起了东起西安,西过葱岭,从喀什出发,穿越费尔干纳盆地,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德黑兰等,到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沿岸的朝觐和商贸通道。蒙元时期,穆斯林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在中南地区也得到深化。(24)以回回为代表的色目人在政治地位上仅次于蒙古人,但在经济和文化上却趋向和依赖于农耕的儒家文明。一方面,受中原农耕文明影响较深的穆斯林日益向东部和南部散居,成为今天所说的“回族”的主体部分。另一方面,大批回回精英如赛典赤、蒲寿庚等在南方任职,推动了穆斯林更大范围的本土化,使唐宋以来海上和陆上而来的穆斯林在中南地区相遇并有了共同的身份想象。南方回回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商贸中心泉州、杭州、广州和占城(今越南归仁)的周边地带,云南的回回在不同阶段由西北迁徙而来,在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所说的“高地东南亚”(High-UplandSoutheastAsia)接壤中国西南的地区形成了人口仅次于西北的华人穆斯林社群。(25)南方回回和云南回回成为后来东南亚穆斯林的主要来源之一。 明清时期,在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中,穆斯林的中国本土化叙事对王朝内部政权的稳固和边疆的拓展与治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以来,“华人穆斯林”的本土化在帝国内部得到巩固,回回逐渐吸收了以汉字、汉语、汉话为载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形成了“回-儒”文化和“回-民”认同,清朝对“回”进行有层次的区分和治理,以“回-民”“回-部”等的方式把穆斯林纳入到了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治理体系中,通过理藩院以“部”之建制管理西域穆斯林,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根据族群特征也因地制宜地自我治理。[8]这种治理形式结合了宗教与政治,身份与认同,以及法律地位与文化归属,实现了在今天看来比较棘手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善治”。 明清时期的“华人穆斯林”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多样性群体,并出现了“回儒”这个独特的文化人类学现象,沉淀了一种“中华为体、回儒兼容”的族群文化。元朝以来,华人穆斯林在人类学意义上已经“华化”。明清时期,穆斯林中的知识分子逐渐开始用汉语著述、阐释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及哲学思想,汉语伊斯兰教典籍即“汉克塔布”(HanKitab)开始呈现。在与汉族士人的互动中,产生了王岱舆、刘智、伍遵契等回儒学者(26),他们“以儒译经”,“以汉地儒学与儒家礼法作为开拓理解苏非、伊斯兰教律法‘前结构’的先声,原创性地以‘性理’解读伊斯兰教苏非,以‘典礼’解读伊斯兰律法。”[9]这种通过汉语翻译和阐释古兰经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方式,实现了经学的中国化和信仰的本土化,汉语特色的“天方之学”成为伊斯兰教对外传播中一个重要的本土化“创制”,[10]伊斯兰文明通过“华化”得到再塑。这种创制在伊斯兰传播史上是罕见的,是注重生活世界的中华文明与强调信仰世界的伊斯兰文明在社会实践中对话的结果。由此,回儒学者们通过证明儒家学说与伊斯兰的可比性,呈现出独特的“华化”的穆斯林叙事。 在对外拓展上,14世纪以来,华穆二元的回回文化,在海上开始向南洋一带传播,在云贵高原一代也开始辐射周边地区。其中,郑和下西洋对华人穆斯林社区在东南亚的拓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郑和所倡导并建立起的这一庞大的海外华人穆斯林网络……赋予伊斯兰教的色彩,然后整合进明朝的海外朝贡贸易圈内,使之成为海外诸蕃与中华帝国维持政治及经济联系的不可或缺的纽带。”[11]根据钱江的研究,“中国穆斯林以占婆为中心,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尼群岛组成了自己的贸易和传教网络。在这一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原籍云南但来自占婆王国的华人穆斯林曾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2]尽管今天学界对于东南亚伊斯兰教由中国传入有诸多争议,但今天泰国(秦和)、缅甸(潘泰)、马来西亚(回族)的部分穆斯林来自中国是确定无疑的,越南、柬埔寨、泰国的占族穆斯林(27),以及印尼泗水、马来西亚马六甲的穆斯林和中国的历史关联也是有史实可考的,甚至印尼前总统哈比比就公开承认印尼的伊斯兰来自中国。(28) 四、“华人穆斯林”对“一带一路”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中医有时以毒攻毒会使用毒性药材,含有毒性药材的中成药应该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不能自行服用,并且需要注意药物的相互作用,中药常见毒性药材如下:马钱子、白附子、附子、半夏、天南星、巴豆霜、山豆根、北豆根、吴茱萸、苦杏仁、苦楝皮、牵牛子、猪牙皂、罂粟壳、贯众、制川乌、鹤虱、川楝子、重楼、雄黄、朱砂、全蝎、蟾酥、蜈蚣。 19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殖民扩张中,如前所说的东亚封贡体系土崩瓦解,周边藩国逐渐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中国古代宗藩朝贡体系下的疆域观念与归属关系,嬗变为源自西方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近现代主权观念下的领土归属关系。”[14]周边的“华人穆斯林”成为西方殖民列强、清政府和当地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由于清朝的衰落,不管是早期欧洲人的殖民统治,还是20世纪亚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华人穆斯林在亚洲国家的权力政治中都处于边缘位置。在清末民初的变局中,孙中山等人“五族共和”的政治构想曾一度把“回民”和其他主要族群置于同等位置。然而,这种构想在内忧外患中以失败告终,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旗取代。20世纪上半叶,在抵御外族特别是日本的侵略中,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得到空前强化,面对中国之外的他族,境内外的华人穆斯林特别是回族保持着对自身“华化”的中国身份的高度认同。(32)二战结束以来,亚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欧美殖民势力陆续从亚洲撤出,以当地主体族群为主导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把穆斯林“少数民族化”,并以“民族”为单位来区分和界定其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和身份。原中国宗藩体系下的“华人穆斯林”群体在所在国则逐渐被“边缘化”,“民族国家”原则的主权观念与边界划分还切割了他们与中国的天然的地缘连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贸经济的发展才使他们通过市场的流动性重新与中国连结。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华人穆斯林通过清真寺、伊斯兰商会等非国家的宗教、文化和贸易网络重新连结起来。年以来,长期以欧美国家为引擎的经济全球化开始衰退,“一带一路”的前现代遗产在亚洲地区被重新发现,与中国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华人穆斯林”对“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33) 当前,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看作是应对资本主义世界新危机和建构新的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尝试,连结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既是一种区域或跨区域的网络倡议,也是一种区域或跨区域的社会实践与跨国治理。“区域是一种非国家的社会历史单元,区域治理是人类基于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族群分布和文明传承而进行的以区域为单元的社会实践。”[15]“华人穆斯林”正是以东亚大陆为实践场域,通过一种非国家的社会、历史和宗教网络,参与了历史上的“一带一路”的社会实践。某种意义上说,“华人穆斯林”是“一带一路”早期的开拓者和实践者,早在欧美人到来之前,他们通过在东亚大陆的迁徙、流动和繁衍把“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连结起来,中国成了一个大的文明交互的中转枢纽,连结东亚、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并分别通过海上和陆上向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的纵深处延伸。挖掘“一带一路”的前现代遗产,对“华人穆斯林”的历史功能进行再发现,有利于形成一种跨文化、跨族群的跨国社会网络,在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提炼独特的东亚历史经验,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包容性的区域或跨区域治理模式。 五、结语 从学术研究上来看,把“华人穆斯林”概念从国际学界引入到国内相关领域的探讨中,有利于国内民族、宗教研究和国际上的跨国族群研究的对接,有利于国际移民、华侨华人和跨国族群等跨学科研究项目的整体推进,在全球视野下达成跨学科研究的规范性共识。从现实意义上看,“华人穆斯林”这一跨国族群概念,把“族群边缘”(34)的“华人穆斯林”作为考察对象和研究视角,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话语重塑至少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对中国境内不同的族群文化进行再认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内涵进行再挖掘,在西方世界之外探索一种与穆斯林世界的共处之道。对中国回儒交融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从华人穆斯林的本土化经验中提炼回儒文明的共同之处,有利于形成华人与穆斯林共有的价值纽带,达成中华文明与穆斯林世界的共识,对中国与穆斯林世界的交往有重要意义。“华人穆斯林”是“一带一路”前现代遗产的最重要继承者,也是“一带一路”上可资利用的“软实力”资源。当然,要注重“华人穆斯林”身份的叠合特征带来的共享性,而不能把它们当作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侨民和移民作为软权力资源,实际上形成了原籍国和现籍国在非国家领域的权力竞争,不过,这种竞争不再是现实主义的‘零和博弈’……‘合作共赢’的建构主义思维逐渐取代‘零和’思维成为主流。”[16]“华人穆斯林”的华人、穆斯林和现居国居民的三合一身份,对原籍国和居住国都有影响力,相关国家宗教、民族和侨民政策将决定“华人穆斯林”的人心归属,中国政府若能制定更具包容性的相关政策,设计一种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政府间制度”(intergovernmentalinstitution),中华文明将依托“华人穆斯林”在穆斯林世界得到认同,中国的软实力自然也会得到彰显。 第二,有利于丰富中华文明关于宗教、民族等的历史叙事,对中国境内原属阿尔泰语系的穆斯林真正融入中华文明体系中有重要借鉴意义。同属一国、同一信仰和类似的历史记忆,是中国境内不同穆斯林族群的共同特征,华人穆斯林是维吾尔族为代表的原阿尔泰语系穆斯林和以回族为代表的汉语穆斯林最大的公约数,然而,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原则和多元“文明国家”模式在中国边疆和周边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交融、又输出了众多海外移民的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下,通过“民族国家”的视野和框架来建构现代国家,局限性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可能。“一带一路”的推进必然带来“华人穆斯林”跨境身份的认同问题,打破“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下的“民族国家”神话,又不走西方经济殖民主义的老路,是跨境民族治理的关键所在。(35)对于“华人穆斯林”特别是少数族裔的华人穆斯林,既要看到他们“华化”、现代化程度的不同,也要看到他们基于伊斯兰信仰带来的观念差别,还要看到他们在不同社会环境形成的群体性差异。挖掘历史资源,借鉴历史经验,丰富中华文明的历史叙事,进而建构一个多元包容的现代文明国家,是中国“多元一体”文明国家建构的应有之义。 第三,有利于在国际社会形成多元包容的现代文明国家形象,为“一带一路”倡议创造一种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华文明,那种过于强调华夏文明或者把华夏文明当作中华文明的“中国中心主义”或“大汉族主义”认知,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并不相符,对中国对内对外的国家形象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36)中华文明对外呈现的应该是一种丰富多样的华人族群的形象,华人穆斯林体现了这种外向的多样性特征。中国“文明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周边族群不断融入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内聚性和包容性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有利于破除工业革命以来对“民族国家”现代性的盲从,中国的“多元一体”模式若能通过新的机制焕发生机(37),将有利于改善“一带一路”上的政治生态。“华人穆斯林”作为“跨国性的华侨华人社会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优秀的文化和发展经验在国际层次的社会化,从而有利于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化。”[17]当然,华人移民海外的过程也是“中国性”“华性”或“华人性”在海外传承、再塑乃至异化的过程。(38)华人穆斯林在海外的“华人性”如何衡量与评估?在国际社会中反馈如何?这是理解华人穆斯林“处境化”生存状况的关键,也是一个与“一带一路”研究密切相关的话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本文的论述,只是提供这个视角的一种尝试。 注释: [1]穆宝修:《元朝回回农耕的土地来源》,《民族研究》年第5期,第61页。 [2]ZhangZhenjiang,“Whydowereferto‘ChineseEthnicMinoritiesOverseas’?-AResponsebyaChineseScholar”,ChineseSouthernDiasporaStudies,Vol.7(-). [3][4]陈志明:《伊斯兰人类学、中国穆斯林与海外中国人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年第1期,第33页。 [5]赵鼎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第9页。 [6]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北京:中华书局,年,第20页。 [7]JohanElverskog,BuddhismandIslamonthesilk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p.. [8]马海云:《清代的族-民政治与回-儒文化》,《文化纵横》年第3期,第34-40页。 [9]马超:《汉克塔布:本土化模式与苏非传统语境研究——以天方性理为例》,《回族研究》年第2期,第53页。 [10]丁俊:《“天方之学”在中国的学术历程与学术精神》,《阿拉伯世界研究》年第2期,第73页。 [11][12]钱江:《从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年第3期,第7、1页。 [13][14]刘晓原:《边疆中国:20世纪周边及民族关系史述》,香港新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年,xix、xv。 [15]张云:《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治理: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年第7期,第页。 [16]张云:《华人华侨在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中的角色研究》,《史学集刊》年第2期,第69-70页。 [17]付宇珩、李一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亚洲秩序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反思》,《当代亚太》年第4期,第34-35页。 Sinicization,DiasporaandGovernance:Astudyonthepre-ModernRelationshipbetween“ChineseMuslims”andthe“BeltandRoad” ZHANGYun (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AcademyofOverseasChineseStudies,Jinan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Abstract:WiththeidentityofChinesebackground,Islamiccultureandlocalizedcitizenship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uyazaoa.com/zyzls/5038.html
- 上一篇文章: 回春大药房冬季阿胶滋补正当时鲜制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