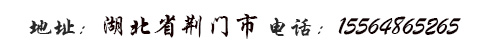清代烟祸军民的鸦片瘾,震惊了道光皇帝
|
北京治白癜风好的医院是哪家 http://www.zykyhs.com 在中国,吸食鸦片的习惯是从吸食烟草的习惯上衍生和发展出来的。在明朝万历年间(—),烟草传入福建沿海,最早种植在漳州的石码镇。之后,烟草种植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很快成为国内重要的经济作物,打破了葡萄牙人企图为他们在巴西种植的烟草建立东方销路的美梦。到了康熙年间,吸烟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全民爱好,石码等烟草品牌迅速占领了北京城中上千家烟草店铺的招牌,甚至于很多烟草就种在城墙边上。 在我阅读到的中文文献中,关于吸食鸦片的最早记录是明代学者张汝霖(卒于年)在《澳门记略》中的记载。张汝霖在介绍了鼻烟之后又记述了关于鸦片的内容:“又有鸦片烟,初如泥,炮制之为烟,有禁勿市。”张汝霖及其家人从鸦片中获得了感官上的愉悦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的第一批烟民。有证据表明,在雅加达的中国人早在年便开始吸食鸦片,在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在年便开始从事鸦片—烟草混合物的生意。关于吸食鸦片的记载出现在年代,爪哇岛的荷兰医生恩格尔伯特·肯普费(EngelbertKaempfer)注意到有商店向行人兜售鸦片和烟草的混合物。台湾的鸦片是从荷兰传入的,早在17世纪,荷兰人就统治了台湾,但是关于鸦片的记载出现得较晚—年,清廷官员蓝鼎元在平定台湾朱一贵之乱以后,才记载了有关鸦片的情况。 蓝鼎元将鸦片比喻为一个危险重重的陷阱,是台湾的蛮族之人想要引诱汉人的武器:“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愚夫不知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特甚殊。”蓝鼎元并没有对吸食鸦片的方法做出详细的说明,仅仅谈到“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黄叔璥则记载:“鸦片烟,用麻葛同鸦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鸦片,拌烟另用竹筒贯以棕丝,群聚吸之。” 这些史料都没有关于吸烟者的详细记载,也没有说清楚究竟吸的是什么东西。蓝鼎元和黄叔璥只是提到吸烟者是罪犯或是受人教唆,而张汝霖根本没有提及吸烟的人。关于禁烟的记载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吸烟的人,但是,这类记载与关于吸烟者的记载类似,最早出现在年的禁烟令只是大体提到“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处置”。 年的禁烟令打击了售卖鸦片的商人,但是对吸食鸦片者却没有形成什么影响,这条法令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尽管没有证据佐证,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吸食鸦片与烟的混合物的现象在18世纪的中国已经蔓延开来。法国商人夏尔勒·德·贡斯当(CharlesdeConstant)记载了年代广州人普遍吸食鸦片和烟草混合物的情景;英国人克拉克·阿裨尔(ClarkeAbel)写道,无论是将鸦片裹在烟叶里,还是将烟叶浸泡在鸦片溶液中吸食,在“帝国各地”都随处可见。 这些扑朔迷离的史料只能让我们大致了解吸烟者是何人、鸦片烟为何物以及何时吸食等问题,有些学者甚至完全拒绝使用这些史料。陈其元阅读了年以后的记载,认为“夫鸦片即鸦片烟,岂又须加入烟草,乃成鸦片烟之事?足见当时吸食者极少,故尚不识鸦片烟为何物耳”。如果我们了解到语言表达中的鸦片其实有两种,就可以解决这一疑问了。18世纪末,大多数中国人吸食的是一种叫作马达克(madak)的烟,它并不是纯鸦片。马达克是未经加工的生鸦片溶于水后的产物,经过煮沸、过滤,再煮沸至糖浆状,与碎叶混合便可吸食。与吸烟草一样,吸食马达克时也使用常规的烟杆,每克大约产生0.2%的吗啡。年黄叔璥对此过程也只是半知半解,才认为鸦片是用“麻”和“葛”的叶子混合而成。当然,这并不是孤证,荷兰人瓦伦汀(Valentyn)提到年在雅加达看到有人吸食马达克,可以作为佐证。吸食马达克,或者是将烟草与鸦片溶液相混合,可以看作从烟草到真正鸦片的过渡阶段。马达克能够带来较为温和的快感—可能与吸几口大麻不相上下—但是当纯鸦片被开发出来之后,马达克便无人问津了。经过恰当的提炼和存放,每单位可吸食鸦片可以产生9%—10%的吗啡。 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切地证实鸦片烟何时成了“纯鸦片”,但是一般认为,中国人于年代开始吸食纯鸦片,这一时间点是合情合理的。年代,贡斯当发现中国人突然间“疯狂地迷上了一种令人陶醉的东西”,这种新的“迷恋”也许可以从成四倍增长的鸦片进口量中得到印证。年,中国的鸦片进口量仅为一千箱,到了年增长为每年四千箱,这是中国吸食鸦片导致需求量大幅增长的结果。尽管如此,这一需求并不是无边无际的。年英印总督希斯丁(WarrenHastings)运了一千箱巴特纳(Patna)极品鸦片到广州,却发现在广州找不到买主,最后不得不以每箱美元的低价给了一个叫辛奎(Sinqua)的人。 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对吸食鸦片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根据前言,这本书成书于年,因而是关于乾隆年间中国人如何看待吸食鸦片的珍贵史料。虽然赵学敏也同意前人所言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的说法,但是显而易见,他在这里讨论的是吸食纯鸦片: 凡吸必邀集多人,更番作食,铺席于坑,众偃坐席上,中燃一灯,以吸百余口至数百口。烟筒以竹为管,大约八九分,中实综丝头发,两头用银镶首。侧开一孔如小指大,以黄泥掐成葫芦样,空其中,以火煅之,嵌入首间小孔上,置鸦片烟于葫芦首。烟止少许,吸之一口立尽,格格有声。 虽说“吸百余口至数百口”可能有些夸张,赵学敏也没有指出在吸食鸦片之前,鸦片是如何在烟灯上加热的,但这也足以说明,此处吸食的毫无疑问是纯鸦片,而不是烟草或马达克的混合物。 尽管当时鸦片已经开始如瘟疫般扩散,但并没有引起清廷足够的重视,直到19世纪初,清廷才采取了相应措施。此后的法令和奏折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些官员吸食鸦片的细节。年,很多宫廷侍卫吸食鸦片,嘉庆皇帝怀疑太监当中也不乏染有烟瘾者。在嘉庆帝驾崩之后,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道光十一年(),内务府大臣进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搜查,发现一批太监吸食鸦片烟已有二三十年,同吸者又有贝子、贝勒等人。而在四个月前,太子少保、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大臣卢荫溥与其他六部尚书、侍郎联合上奏了一份鼎鼎有名的奏折,指出吸食鸦片者甚众,而奸商贪官是烟患的罪魁祸首。“(窃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其始间有劣幕奸商,私自卖食,浸浸而贵介子弟,城市富豪,转相煽诱,乃沿及于平民。”“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 毫无疑问的是,年的军队中已经烟瘾成患,以至于无法形成战斗力。道光十二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的部队在镇压广东连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近湖南和广西边界)瑶民起义的战争中惨败,据钦差大臣禧恩奏:“该省调至军营战兵六千余名,不惯走山,沿海各营兵丁,多有吸食鸦片烟者。兵数虽多,难于得力。该省营伍,皆属总督统辖,如果平素整顿操防,实心训练,一兵得一兵之用,何至临阵恇怯?” 事态的严重性惊动了道光皇帝和朝廷大臣们,朝廷当中关于鸦片的讨论趋于白热化,年主张鸦片合法化和主张禁绝鸦片之间的争论达到了最高潮。有关烟患蔓延的最为生动的描述出现在年朱嶟的奏折之中,他在奏折中声讨了以许乃济及广州学海堂为代表的弛禁派。弛禁派主张,“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任令沾染恶习”,“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而朱嶟指出,允许鸦片纳税进口,“其言不顺,其名不美”,根本无法杜绝鸦片交易。“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于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 鸦片开始向平民百姓蔓延,可以从三种史料中得到佐证:进口数据、国内产出统计,以及有识之士的估测。 首先是进口数据。年以前,从孟加拉、马尔瓦和土耳其进口的鸦片数量一直保持在四千至五千箱;到了年代,这一数据陡增为一万箱;年再次激增为一万八千箱;年已经超过了两万箱;年达四万箱。增长趋势毫无衰减迹象,到了年达七万六千箱,年八万一千箱。进入20世纪后,鸦片进口量开始减少,稳定在五万箱左右。因进口鸦片质量优良、味道浓郁、劲道浑厚,大多被富人消费。 中国国内种植鸦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当时在中国西部省份,尤其是云南、四川和甘肃等地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罂粟。根据各地地方志的记载,到了清朝初年,贵州、福建等地也开始种植罂粟,但是对于种植方法及其用途尚无说明。道光十六年(年),许乃济在奏折中指出,“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为了论证他的弛禁论,许乃济指出,“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他还举例说道,“前明淡巴菰,来自吕宋,即今之旱烟,性本酷烈,食者欲眩,先亦有禁,后乃听民间吸食,内地得随处种植,吕宋之烟,遂不复至,食之亦竟无损于人”。但是,许乃济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因为更受富人欢迎的是进口的烈性鸦片,而不是温和的土鸦片。康熙年间最负盛名的医学家张璐在年写道,“土鸦片亦能涩精止泻,但力薄少效”。到年代,进口鸦片和土鸦片的差距仍然存在,而此时中国的鸦片种植已经扩散到广西、湖南和湖北等地。据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估计,年广西的土鸦片产量在八千担到一万担之间,在国内非常畅销,常常用来与洋烟做比较:“闻起来与巴特那鸦片类似,但不如孟加拉鸦片劲道……若存放两年,则胜于洋烟。”而另一方面,福建的土鸦片“质量低劣,口味粗糙,难以与进口鸦片相提并论”。不过,这种次等的土鸦片价格低廉,每担约价二百五十元。而据许乃济的记载,进口鸦片价格高昂,进口鸦片之类有三:一曰乌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买;一曰红皮,出曼达喇萨。乌土为上,每箱约价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价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价四百元。 广东地区并非土鸦片的主产区,由此可以推测西部省份的土鸦片产量应该远远高于八千担的水平,内陆地区鸦片的价格也应该比二百五十元更低一些。因此,中国的鸦片产量和消费量都远远高于年英国领事估计的数量——也远远高出了赫德于年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做了一番调查之后所给出的估计量。这样看来,最初以占有有钱人鸦片市场为目标的土鸦片,最后恰恰是满足了苦力们的需求—特别是轿夫和船夫。到年代,中国苦力吸食鸦片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除了价格低廉—在甘肃,印度鸦片的价格高于土鸦片十倍有余——此外,中国的土鸦片还有一个优势,其残留烟渣也可以用来吸食,而印度鸦片就难以实现这一点。 根据当时满人的描述,中国的工人也乐意接受掺假的鸦片—不仅仅是掺杂罂粟壳或罂粟荚,同样也掺杂猪油、芝麻籽、柳叶芽和蓟汁。尽管有钱人一般是将土鸦片与印度鸦片混合后吸食,但在弹尽粮绝之际也会转向土鸦片。年到年芝罘一带长年饥荒,富家子弟也不得不节俭开支,转而吸食土鸦片了。后来,他们逐渐习惯了土鸦片,并不再迷恋于进口鸦片,结果这一地区印度鸦片的销售量猛跌。随着中国的鸦片种植者明智地开始提高土鸦片的质量,越来越多的人吸食土鸦片,消费土鸦片的富人也与日俱增。 我们同样可以推测农民吸食鸦片的情况。大约是在年代,中国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吸食鸦片,这一时期土鸦片的产量增长迅猛。鸦片的种植刺激了种植者自身吸食鸦片,之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事实。美国学者卜凯(J.L.Buck)全面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他发现农民自己的鸦片消费量约占其种植量的四分之一。尽管鸦片的产量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但是作为一种经济作物,种植罂粟还是利润颇丰的。一亩罂粟至少可以生产出两倍于谷类植物的利润;每年10月份种下去的罂粟,到了第二年3月即可收割,恰好在这段时间内其他农作物也没法生长;要是有足够的肥料,罂粟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还可以与豆类、土豆或烟草套种。对于佃农来说,在租赁的土地上进行冬季种植更是利润丰厚—因为他们只需要按照夏季作物产量的某一固定比例上交地租。77不仅如此,虽然采集罂粟汁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技术难度不大。 渐渐地,人们也在质地良好的土地上种植罂粟了。不妨将李希霍芬(BaronvonRichthoven)在年的调查结果与斯宾士(W.D.Spence)年的调查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发现中国西南部罂粟的种植已经从山地转移到了河谷地带。赫德试图以人口数量和罂粟产量的比例来估计中国的烟瘾程度,最后得出吸烟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比例太低了—张之洞坚持认为,在山西,城市的吸烟人口比例高达80%,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也高达60%,而曾国荃认为农村的吸烟人口比例高于城市,在甘肃有人也认为这一比例高达80%。我们很难判断准确的数据是多少,但是理雅各(JamesLegge)提出的10%的估测似乎比较合理,这个比例是理雅各乘坐小驴车颠簸着前往孔庙的途中,根据山东的罂粟地估算的。理雅各的推断可以与经验丰富的雒魏林博士的数据相互印证,雒魏林估计中国有10%的人口吸食鸦片,但是只有3%至5%的人口“过度”吸食。根据这个估计,年中国有一千五百万烟瘾人口,如果他们每天吸食三分之一盎司的鸦片,或是每年吸食七磅的鸦片—这是华人学者普遍认同的数量——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消费掉一亿五百万镑的鸦片。那么根据这一推算,年代四川八万五千亩地生产了十七万七千担鸦片(两千三百五十万镑),平均每亩只生产五十盎司,这显然就不合理了。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对20世纪的鸦片销量进行反复核算,以获得更加精确的数据:云南昆明约有两万九千七百五十亩罂粟地,仅四川涪州的鸦片产量便为两万三千担,山西约有一百万亩罂粟地,陕西约有五十万亩罂粟地和一百五十万人口吸食鸦片。对于世纪之交的地区贸易而言,一般的估计认为:国内每年约有一亿两白银的大米交易,一亿两白银的食盐交易和一亿三千万两的鸦片交易。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有大量人口在吸食鸦片。 本文节选自《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由过客·History授权转载 作者:史景迁,译者:钟倩,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理想国 佳作推荐从酒精到芬乃他林——战争中的精神药物 从荷马时代的战士饮用葡萄酒,到德国国防军给士兵分发苯丙胺,精神药物可谓是伴随着人类走过了无数场战争。在本文中,我们将回溯过去,看看到底有哪些精神药物在人类的战争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点兵堂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uyazaoa.com/zyzxf/5212.html
- 上一篇文章: 这个BIM,比百度百科还全面,让你更加深
- 下一篇文章: 年连锁药店补益类黄金单品卖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