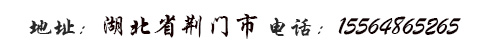书香天府middot全民阅读迎
|
儿童白颠疯如何确诊 http://news.39.net/bjzkhbzy/180108/5985095.html 迎风山上的告别 作者:章泥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二章 13.红与蓝 “对,我们回去就是要把这些特殊的情况梳理出来,给督导组报告。陈贵群,我们接着往下说,再看看你家的基本医疗有没有保障。你家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没有?建档立卡没有?” “新农合啊?参加嘞,参加嘞。” “新农合,这个全村都参加嘞。” 黄支书在一旁补充道。 爸爸的回答都很简略,大个子叔叔问的好多问题,黄支书都要适时帮补一下。黄支书帮补的时候,嘿嘿嘿,爸爸就立在旁边附和着笑。 “第三个,是住房安全有保障。你家这房子面积倒是不小,还有个院坝,这样的一块地,放在城里,要让好多人羡慕。” “呃,可惜这些土地在农村又不值钱。” “你家房子,有七八十年了吧?我们察看了,老土墙勉强将就,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行了。门窗破烂,可能从来没有维修过,灶房还漏雨,柴棚架上的瓦都要掉光了,你家纳入危房改造没有?” “莫有。” “是莫有,”黄支书忍不住又接过话来,“他家之所以莫有纳入危房改造,是计划对他家进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前一阵,乡上和县上的同志都来看嘞,说他家住得这样偏僻,左邻右舍莫得一户不说,这山腰嘴上,又临崖又朝阴,地势不好,如果有个山体滑坡,他屋第一危险,所以建议他屋易地搬迁。我们也和他沟通商量嘞,是不是,独眼儿?这些话,你要对督导组的同志讲啊。” “嗯啦,嗯啦。” “‘三有’应该都有了吧?” “有嘞,有嘞。” “电是全村都通嘞,水,他家取的是地下水,这匹山其他没得啥子好的,就是水还清亮得好。这儿的水,打起来可以直接往肚皮里灌,比起商店里那些装在瓶子里卖的矿泉水好到哪儿去嘞。” “水好不好,不能只是凭眼睛看到清亮就说好,要送去检测,对水质要有鉴定。新房子建成后,通自来水吗?” “通,那肯定是要通嘞。” “现在这儿通广播电视没有?” “通,通嘞。” “通是通嘞,只是他家看的听的啥子东西都莫得,电视机不说,收音机都莫得一个。” “我看你有个手机,信号怎么样?” “信号好,满的。” “去年,不,应该是前年县移动公司到万顺乡上搞网络覆盖时,乡上就争取到给全乡所有贫困户每户发一部手机。他这个也是当时发的,是吧,独眼儿?这种手机屏幕虽然小,上不起网,是他们说的啥子老年机,但是很实用,声音又大,信号又强,大家拿在手里,至少有个通信工具。而且,他们话费都不用缴,这些移动公司全免嘞,拿到这个手机,大家确实还是很受益。是不是喔,独眼儿?” “嗯啦,嗯啦,谢谢喔!” “贫困户脱贫,贫困村退出,其中关于有广播电视这一项的考核指标是很硬的,要求贫困户户户有电视,贫困村村村通广播,达标率要百分之百。” “现在,电是有的,网也是有的,只是他屋暂时还莫得电视机,我们村上,莫有电视机的还有好几户,也不多嘞,到时候,易地搬迁,住进新房子,都要给他们配,县上的规划我都看到嘞。所以啊,独眼儿,你应该再睁开一只眼,看看马上就要来的好日子!” “嘿嘿嘿,真的啊?” “那还有假话啊?要说假话,我不晓得悄悄给你说,要当着省督导组的同志给你说?既然是当着督导组给你说嘞,那肯定莫得假喔。” “喔,喔,谢谢喔,谢谢!” 爸爸又是一阵点头弯腰。听他们说来,我家以后也会有电视了。想起那个有猫和老鼠在里面互相捉弄的方头方脑的家伙,我的心忽然突突突突地蹦着。脑子里又浮出我在瘫子家和他一起看《猫和老鼠》时笑得前俯后仰的情景,我又听到我们哈哈哈哈的笑声,只是不知道,妈妈和弟弟如果也看到电视里的《猫和老鼠》,他们会笑吗? “谢谢你!” 这次,大个子叔叔反过来对爸爸说谢谢了。为什么要谢爸爸呢?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大个子叔叔接着说: “谢谢你配合我们完成了这份调查。” “你能认字吗?” 正在柴棚边整理袋子和一大叠表格的“白围巾”突然问爸爸。 “能,能。” “你能签字吗?” “能。” 爸爸又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请你看一下,这一套表格我是按照你家的实际和刚才的调查来填的,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请在户主这一栏签上你的名字。来,用这只黑色的签字笔。签好名后,这儿有印泥,请在你的名字上盖上你的手印。” “白围巾”说着,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小圆盒,“银帽子”帮着“白围巾”把小圆盒打开。“白围巾”又从袋子里随手抽出一本小册子样的东西,垫在表格下,让爸爸签字、盖手印。 我很想走过去看看爸爸写的是什么,却迈不开腿。我不知道我走过去会招来什么样的结果。黄支书不是给他们说我会咬人吗?我真怕自己这一走过去,把大家吓得东跑西蹿。也许,憨子加哑巴的我,就和他们保持这样一小段距离,不仅对他们、对我自己也是安妥的。 我就那样原地不动地站在院子里,头昂向一边。这模样,不用照镜子,我都知道自己像极了那天秃顶伯伯带来的钉子一样钉在我家院子里的那个男孩。 “谢谢!” 爸爸大概是签完字,也盖完手印了。“白围巾”也对他说了个谢谢。今天真是奇怪了,我听见他们好几次对爸爸说谢谢。 “白围巾”看了看爸爸写的字,笑着对爸爸说: “你写的字,还很工整呢。这两个孩子,他们叫什么名字?也写上去吧。” “写得不好喔,让你们见笑嘞。” 爸爸嘿嘿笑着,怪难为情似的。 “人家独眼儿是读完小学的。是吧,独眼儿?” 黄支书打趣着爸爸。 “嗯啦,嗯啦。” 爸爸认真地答道。 “写上吧,”“白围巾”再次说道,“把你家这两个娃娃的名字都写上。” “嗯啦。” 爸爸又有了一次写字的机会,我斜着眼瞟见他在“白围巾”他们帮忙为他垫着的刚才签字的表格上又认真地写起来。 “陈又木。老大叫陈又木?” “白围巾”问。 “嗯啦。” “陈又林。这是老二?” “嗯啦。” 爸爸一笔一画终于写完了,我昂在一边的头忽然垂了下来。 “陈又木”,我叫陈又木吗?我都快忘了我的名字。这个家,平常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更没有谁叫我的名字。爸爸实在要喊我一声,都是叫我“大砍脑壳”“大狗日的”“大挨刀”“大憨”“大瘟丧”“大短命”……“陈又木”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已经陌生得像遥远世界里的奇花异草。 我的头越垂越低,垂到不能再垂的时候,我恍然明白妈妈和弟弟为什么常常各自在神游、沉潜。他们是在那遥远的世界寻找他们的名字吗?寻找他们名字花冠下芬芳四溢的另一个自己吗?他们为何先我一步?我不是常常觉得自己比他们都灵醒得多吗?为什么我和我的名字现在都还身首异处? “走吧,叶珂琬,彭澎,”大个子叔叔喊着“白围巾”和“银帽子”,“我们去下一户,黄支书,还是你带路哈。” “走吧,独眼儿这一户还好,屋头莫得狗,其他几户都有狗,要小心点,我走前面,喊他们把狗套着。” “白围巾”忙着收拾放在柴棚架上的一摊表格,她正要扣上手中的塑料袋,忽地想起什么。她伸手往袋子里掏了掏,摸出一支蓝色的笔。 “来,这个送给你。” “白围巾”走到我面前,伸手把笔递向我。 这是给我的?一支笔?一支蓝色的笔?我抬头望着一下走到我身边的“白围巾”,心里紧张得几近惶恐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我可是从来没有奢望过要得到笔这样的东西。笔这样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就像电视里的猫和老鼠,它们虽然在我眼前眉飞色舞地蹦跶着,让我无比开心,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样的猫和老鼠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猫永远要像婴孩啼哭一样叫唤,现实中的老鼠,永远要在我们的脏衣服堆里穿来穿去。曾在我眼前蹦跶过的笔,怎么会真真实实属于我? “拿着吧。” “白围巾”把笔递得离我更近了。我轻轻伸出手,慢慢张开。我之所以这么轻这么慢,实在是怕我急起来快起来,吓着她。我为自己咬过人的曾经感到羞愧和无奈,我多么怕再次吓着别人。 而她是那么勇敢,面对有一副会咬人的牙齿的我,她居然在把手伸向我的同时保持着镇静和微微的笑。 我终于在原地接过了那支笔。接到笔,我马上又垂下了头,我把笔攥得紧紧的。没错,这是给我的,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支笔已经是我的了。没错,没错。我自己安抚着自己,完全忘记了对“白围巾”说声谢谢。 “谢谢”这两个字,我不是已经练习过很多次吗?我不是自认为把“谢”和“十”都可以分清楚了吗?偏偏这会儿正该说出它的时候,我又忘了开口。 我再次抬起头的时候,“白围巾”已经转身从我身边离开了。我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背影,这时,我才注意到她围着的那条白围巾毛绒绒的,像一枝雪白而蓬松的芦苇花。这枝雪白而蓬松的芦苇花几乎把她的半个后脑勺都捂在了里面。 “白围巾”经过弟弟身边时,弟弟也抬头望了她一眼。弟弟暂时从他自己的王国里抽身回到了眼前的院坝,他也知道此刻又该有一场告别?他的大眼睛愈加黑白分明了,污渍秽迹让他二指宽的脸颊显得更为寒凉。他的目光一定碰触到了“白围巾”,“白围巾”在他面前停了下来,她又打开怀中的塑料袋,伸手往里面掏着什么。 “这个给你。” “白围巾”递给弟弟一支红色的笔。弟弟伸手接住了。 “再见,陈又林。” “白围巾”边扣袋子边对弟弟说。 “还有你,陈又木,再见!” “白围巾”回头也叫着我的名字,对我大声说了个再见,就小跑着跟上大个子叔叔他们出了门。 “白围巾”的身影从院子里消失了,但她喊着我和弟弟名字的声音的影子却留在了院子里。 “陈又木……” “陈又林……” 几乎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她这样用我们的名字喊过我们,我的耳朵和脑子似乎都还有些不适应。 他们都走了,我这颗钉子终于可以活动了。我走到弟弟跟前,瞟了眼他手中的那支笔,他的笔是红色的。还有红色的笔吗?我见过黑色和蓝色的笔,这两种颜色的笔,瘫子都有,但我从来没见过红色的笔,红色的笔写出的字也是红色的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一把抢过弟弟手中的笔。正沉浸于一树花香的弟弟突然从树上掉下似的大哭起来,边哭边向我扑过来要抢回他的笔。 “挨刀的,又角逆!有啥子稀奇嘞,搞啩一半天,老子瞌睡都莫有补成,一分钱莫给,还啥子省上来的,枉自!打发两根笔杆杆,你两个短命的还有脸争,再争,再争看老子一把撇断嘞了事,砍啩树疙蔸免得老鸹叫!” 爸爸这一吼立马镇住了我和弟弟。 我赶忙抽出蓝色的那支还给他,没想到弟弟不依不饶地就要他那支红色的。他又哭哭嚷嚷地,我只好收回蓝色的笔,把红色那支还给了他。 14.水泥 爸爸转身往屋子走去,准备继续补瞌睡。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他的手机又无所顾忌地唱起来。 “独眼儿!你咋个搞起嘞!刚才小武书记在工地上清点水泥,说昨天下午都有二十六包,现在咋个只有十八包?是不是晚上遭贼娃子偷啩啦,你守夜是咋个守的喔?还不加紧来看,到底咋回事!找不到水泥,是要喊你赔的喔!” 不知是谁,在电话里大声嚷着。 “啥子唉?”爸爸更大声地嚷着,“不可能喔,我马上来看!咋个会丢那么多水泥!” 爸爸收起手机赶忙又去发动他的摩托车。 “真是撞到个鬼嘞,钱没有挣到一分,还想喊我赔,赔你个脑壳!” “不——不——不——” 爸爸气冲冲地出了门。我和弟弟面面相觑,好像刚才我们的争闹引出了这场祸事。我站在院门口往山脚望去,一半灰蒙蒙一半素面朝天的道路上,一群人在旁边围作一团,都要中午了,不见那些机器开动,也不见谁像往日一样拿着锄头、铁铲挖挖刨刨,到底怎么回事?爸爸守夜真的丢了水泥?他们真的要他赔吗?我感觉到自己的双眉越拧越紧,紧得要打成死结的一刹那,天空对着我的头顶哗地沉下来,我慌忙沿着土路往山脚跑去。 “我又清点了一遍,确实是少了八包。” 小武的额头上浸出一层密密的汗,一眼看上去,他就像一棵还挂着露水的庄稼。 “那我不晓得,反正我昨晚一晚到亮来来回回都在这条路上走。” 爸爸斜靠在他的摩托上,脸上的恐慌没有了,委屈没有了,只有满面的漠然。 “你在守夜,你总得对这件事负责啊!”刘村儿吼着,“不要给我耍赖皮!” “我看,我们关键是要找到这八包水泥的去向。陈大哥,你说你昨晚一晚到亮都在路上来来回回地走,走的是不是只是这半段土路?铺了水泥的那半段还在保养,你肯定没有在上面走,对吧?” 小武擦了擦额头,问爸爸。 “你们说才铺了水泥的路面不能踩啊,我当然不敢踩。反正我都是按你们说的在办,好说歹说,都是你们在说,现在出问题嘞,你们全都推给我,屎盆子一把扣在我脑壳上,凭啥子?到底是哪个在耍赖?”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小武接着爸爸的话说: “很有可能是,陈大哥走到土路那端时,小偷沿着边沟从铺了水泥的这端偷走了水泥。” 小武话音一落,大家似乎觉得有些道理。 “独眼儿,看来贼娃子比你狡猾喔!” “现在一包水泥好贵嘛,搬几包回去,相当于赶个猪儿回屋!” “一晚上六十块钱不好挣啊,独眼儿,还是回屋钻到铺盖窝窝头热和舒服!” “哎哟,这八包水泥要是喊独眼儿赔,也太划不着嘞,守啩这么久的夜,一分钱莫挣到,还要倒赔,独眼儿,你硬是倒嘞八辈子的霉喔。”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一股无形的火越扇越旺。 “查!挨家挨户地给我查!我不相信找不到这八包水泥!” 刘村儿硬邦邦甩下这句话。 “刘村儿,小武书记,我看你们找守夜的人还是找个灵光点的嘛。陈独眼儿,不是我损他,莫说他在这条路上一晚到亮地走来走去,就算他在这条路上一晚到亮地爬来爬去,他也只有一只眼睛!这么长的一条路,他一只眼睛咋看得过来嘛?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你们看到嘛,这样下去,这条路上肯定还要丢东西,今天丢水泥,明天丢工具,后天说不定就把那几台机器给你们开跑嘞!换成我来守夜算啩啦,我再背时也有两只眼睛,脑门上这个瘤子,到晚上,贼娃子还以为是我长的第三只眼睛,把我当二郎神,看哪个还敢来偷东西!” 嘿嘿嘿嘿,一群人都被钟瘤子逗笑了,只有爸爸的脸垮得更厉害。 “你!你会算计!口中夺食!” 爸爸吼向钟瘤子,钟瘤子嘿嘿嘿嘿笑得更惬意了。 不知什么时候,黄支书也赶来了。他掏出烟点上,猛抽了两口,干着嗓子喊道: “莫说这么多!各人都去干活,该干什么干起走!还盯到我们看,看啥子?我们没得脑壳啊?我们下来马上就要想办法,一是要尽快把这个月的工钱给你们几爷子兑现,二是要找到这八包水泥,我不相信,哪屋的人还可能把这八包水泥煮来吃啩啦!” “来嘛来嘛,把活路弄起走!” 大家陆续散开,不一会儿,锄头铁镐铁铲都丁丁咣咣地挥的挥,舞的舞,那几台愣头愣脑的机器也轰轰轰地像几头大牲口似的叫起来了。 爸爸扭过他的摩托车,“不——不——不——”往山上一腾一腾而去。大家都各自忙活,只有我闲着无事。好在我站在路边的一小片宽敞处,也没有妨碍着、招惹着谁。我在原地蹲下来,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蹲下折着自己、皱着自己似乎好受些。 “刘村儿,挨家挨户去查那八包水泥,我觉得不妥,这样做是不合法的。” 黄支书、刘村儿、小武从我背后走过,他们边走边说话。 “我说要查就要查啊?吓下那几爷子!” “十多年前,隔壁的罗沟村因为弄丢一袋化肥,冤枉一个瘸子,那个背时瘸子当天就在屋头上吊啩啦。这种事,现在要是再发生,哪个担得起?短斤少两,本来也不是个啥子大事,莫弄凶啩啦。” “嗯啦,修一条路,丢几包水泥,我们也是丢得起的。再说,到底是哪个龟儿偷嘞,我心中也晓得个八九不离十。” “那怎么办啊?” “咋个办?凉拌起,拖起。农村里的事就是这样婆烦得很。很多情况,你不清楚,就莫要去管,你去管,他们也不见得听你。你只消把你自己该做的捡大头做好就行嘞,眼下就是要把路顺顺畅畅修出来。其他工作,我做不好,还有黄支书,他说话,还莫得哪个不听。” “对嘞,叫虎子,把工地上的账单和大伙的工钱算清楚,一个月嘞,该给大家伙兑现的要兑现。” “那晚上的工地还要陈大哥守吗?” “这个陈独眼儿,就是一粑扶不上墙的稀牛屎!给他找了个这么好的活路,不出任何本钱,不使力不费劲,耽搁掉的瞌睡白天还补得回来,一个月三十天,一晚上六十块,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千八啊,每个月他要是能挣这么多,他屋早就脱贫啩啦。就是这么好的活路,他也弄不醒活。你们看,今天说风凉话的人都有嘞,到时候说不定又要骂我们一碗水端不平不说,还要告我们从中得啩陈独眼儿啥子好处,这么向着他!” “钟瘤子想守,让他来守就是嘞。他屋也恼火,手心手背都是肉,两个都要照顾到。” “只是守夜的工钱总共只有六十,就让他们两个平分,一个三十,一个人一个月也可以挣将近一千块,也是提到灯笼找不到的好活路。” …… 他们三个从我背后越走越远,往下我再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我就蹲在地上看向那些干活的人,这才多久,这条路在他们手上已变出另一番模样。铺上水泥的那一段路,还没有人走,看上去,平平整整的路面就像湖面上结的冰。我想象着走上去脚底的感受,会很凉吗?会一脚踩破吗? 我走过去,伸手触了触水泥路的边沿,硬邦邦的。我又用劲戳了戳,这下更明显地感觉到它的铁实。原来,这就是他们说的“硬化路”! 我还在琢磨新修的水泥路与我平常走的土路有什么不同,不远处又有一帮人嚷起来。怎么回事?今天这条路好像是一根长满刺的荆条,不是这儿要戳人,就是那儿要戳人。 15.石头 一个背驼得厉害的爷爷正对着那台长着长长臂膀的机器骂骂咧咧,机器停了,上面跳出一个满面胡子的叔叔来。 “你咋个在开喔?石头包块都滚到我地头来嘞,莫生眼睛还是眼睛瞎嘞?菜都给我压死啩啦!” “大爷,我刚才一下没弄好,掉些石头在你地头,也不是故意的,你咋个张嘴就骂人?” “我骂人嘞?我还要捶人嘞!修条路,把我屋的菜弄死那么多!前一阵,我的猫儿钻到你们机器下,毛都给它扯掉一半!修啥子路喔,以前的路好好的走不得啊?修条路你们倒是在里面有搞头喔,有的人怕是捞肥嘞,油都把你们眼窟窟蒙花啩啦不是?” “段驼背,算嘞,人家师傅又不是故意的。” 这个驼背爷爷就是段驼背? “不是故意?滚那么多石头包块,你去给我捡起来啊?我老得快入土的人嘞,背也背不动,扛也扛不起,不可能就让那些石头包块摆在这儿算啩啦!它们一分钟在我田地头摆起,我就一分钟横在他机器面前!老子今天就睡在他机器轮脚,看哪个怕哪个!” “你这老头儿咋兴倚老卖老?你是不是得红眼病嘞?” “哪个倚老卖老?哪个得红眼病嘞?你把话给老子抖清楚!要不然老子今天真的倚老卖老,又咋个?你还敢啃老子一口!” 段驼背气嘘嘘上前几步,更大声地指着胡子叔叔吼道,“你用石头把我的菜压死,我不晓得用石头把你的机器砸个稀巴烂!” 段驼背说着,捡起地上的小石头就朝胡子叔叔的机器砸去。啪啪啪啪,石头冰雹一样砸在机器上,胡子叔叔火了,跳起脚要过去揍段驼背,周围的人都把他拦着挡着。 “算嘞,段驼背是老人,今年都七十多嘞,你惹不起!” “哪儿有这样的老人!我看他越老越不是个东西!” 胡子叔叔蹦着还要凑上前去。 “胡子,莫去惹!” “忍到!年轻人要忍得住!你要是忍不住,他一身的病都栽给你!” “等驼背使使气,他那几颗石头子儿也砸不烂你的大机器。” 胡子叔叔果然只好在原地跳着蹦着,不敢上去动段驼背半根毫毛。段驼背越扔越起劲,最开始还是一只手一只手地捡起石头扔,后来是两只手两只手地抓起石头就扔。大大小小的石头飞往机器,又呯呯呯地弹向四方。 “啊——” 一颗从机器上弹起的石头正正射向我的脑门,我尖叫一声,像一只被弹弓打中的飞鸟,啪地从天空摔落到他们面前。我的眼睛里一片金光灿烂,太阳火辣辣烘烤着我,血很快模糊了我的脸。 “哎呀!段驼背,你把陈独眼儿屋的大憨的脑壳打破个洞嘞!那娃儿本来就憨,这下更憨啩啦!段驼背,现在你安逸嘞!” “快,快抓把土给大憨糊上,先把血止到!” “不行!” “要不得,这些土办法,要感染嘞。” 黄支书他们三人转了一圈,正好又回到这段工地。 “怎么流这么多血,我来看看。” 小武取下他的双肩包,急慌慌从里面翻找出一包纸、两个小药瓶和其他几样东西。 “小武书记,你背的是个百宝箱啊。” “小武书记,你的东西还齐全喔。” “我是养成习惯了,才到村里来的时候,上山下地,又招虫子叮又招狗咬,干脆把一些常备药带上,临时也可以应个急。” “嗯啦,现在不是正用上嘞。” 小武把拿出的东西放在地上的双肩包上,他扶着我的身子,看了看我还在浸血的脑门。 “不要紧,应该没什么大事。” 不知他是在安慰段驼背还是安慰我。 小武先用软软的纸把我脸上的血迹擦了,又拿起一个小药瓶朝我脑门喷,一场小雨向我额头洒来。 “不要怕,这是碘伏,消毒杀菌的。” 随后又用几大根白火柴一样的东西在我脑门上轻轻擦了擦,最后叫我仰着头,他把另一个更小的瓶子里的灰粉粉抖了些在我的伤口处。 “这个不是泥巴灰吗?” 旁边的人问他。 “这是云南白药,止血的。” 说来也怪,我额头上的血很快凝住,没有再往外浸,大家都看稀奇般看着我,有的人欣喜,有的人一下泄了气似的失望起来。 “还是药的效果快。” “哎,段驼背,还以为你今天摊上好事嘞,可惜好戏只开嘞一个头。呃!” “好事,坏事,我怕啥子事!老子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还有啥子好怕的事!” 段驼背的口气又硬起来。 “才转过身,你们几爷子就要闹翻天,都是四五十岁、七八十岁的人嘞,我看你们淘神、角逆来,跟两三岁的细娃儿也差不到好多!到底又咋回事嘛?” 黄支书把烟屁股摔在地上,用脚一跐。 周围人眉飞色舞把石头滚下田的前前后后大致说了。 “那还不简单,石头滚下去,捡起来就是嘞。胡子捡大的,驼背捡小的。再有看稀奇的,跟到下去一起捡!” 黄支书一说,原本僵持不下的段驼背和胡子叔叔都没什么好再扯来扯去的。站在旁边,我一下也觉得刚才还气鼓气胀的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胡子叔叔捡大的石头,他没啥好说的,大的重是重,没多少块,搬完了事。段驼背呢,捡小的也不吃亏,小的虽然多,但是不费力,况且他刚才捡来砸机器都捡了一堆了。守在旁边的,也有人跳到地里去,帮着胡子搬大石头,还有人拿着铲子帮段驼背铲小石头。 “对嘞嘛,几下整完,各人又去干活,今天要给你们发工钱啰。” “今天就发工钱嘞?” 大家的脸一下放着光,就像爸爸的摩托车打开了灯。 “今天当真就要发嘞啊!” 盼望已久的日子一下来临,大家好像又嫌它来得太快了些。听到要发钱,我的脸上也发着光,我知道爸爸也会领到钱了。“不——不——”还负着伤的我,这会儿甚至想跟爸爸的摩托车一样,在迎风山上一腾一腾地奔起来。 大家干活更卖劲了,还在田地里的段驼背脸色愈发跟泥土一样黯涩。 “莫去惹他。” “他领不到钱。” 几个人小声说着: “段驼背真是老啩啦,不能再到工地上挣钱。再有,他屋不是贫困户,这次派工也派不到他屋的其他人,所以他见哪个都丧着个苦瓜脸。” 小武在收拾拿出来的东西,他就要拉上背包拉链时,我又看到了他的双节棍,看到这根打狗棒,我一下咧开嘴角笑了。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小武对我做了个鬼脸,“脑壳上的伤疤不疼了?接到!海苔饼干。”他又朝我甩了个什么过来。 秃顶伯伯上次带到我家来的一大包食品中,也有饼干,只是和小武给我的这种海苔饼干的味道不一样。秃顶伯伯送来的饼干是甜酥甜酥的,海苔饼干的味道有些咸。 “不要乱跑乱动,免得震到你的伤口。我要回村委会,你干脆跟我一起去,让卫生室的人再帮你看看,需不需要再处理一下。” 小武背上双肩包,身子往前一耸,勒了勒两根背带。 “走吧。” 他招呼着我,我跟在他身后,嚓嚓嚓嚓嚼着饼干。村委会离这段路不远,我和爸爸赶场的时候都要经过它,只是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有几座砖房子的院坝就是村委会。 我跟着小武走上院坝的一小排阶梯,到了一间房门口,小武对着里面那个穿着白褂子的年轻女人说: “何医生,这个娃儿的脑门,被一颗小石头砸破了皮,起了个包,我给他敷了点云南白药,你看还要怎么处理一下不?” “哪屋的娃儿喔,咋个没去上学?到哪儿调皮捣蛋去嘞?” “陈大哥家的。” “哪个陈大哥?” “就是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陈大哥。” “陈独眼喔,你是他屋的?” 何医生有些惊讶地望着我,我还在嚓嚓嚓嚓地吃饼干。 “这个是老几?” “老大。” 小武帮我答着。 “你叫什么名字?我要登记一下。” 何医生又问向我。我嚼着饼干的嘴巴停了下来,我想告诉她我叫陈又木,但是这三个字我一个都还不会说。我只好看着她,继续又嚼着嘴巴里的饼干。 “他不会说话。” 小武有些遗憾地对何医生小声说道,似乎怕我和别人听见。 “听说这两个娃儿不仅哑,而且憨,跟他们妈一样?” 何医生反而问得更大声,只怕我和别人听不到似的。 “这个是老大,要好点,他自己虽然不会说,但是别人说的,他大概晓得一些。” “难怪没上学喔。来,坐在这儿,我看看。” 何医生这才指了指她桌子旁的一根板凳,拉我坐下面对她。 “没得啥子事,不恼火,针都不消缝,敞着还好得快些。你看他还晓得吃东西,证明也莫有伤到他啥子。包也不消包,细娃儿,好得快,结啩疤,几天就好嘞。” “那就行。呃,我想起了,这个娃儿好像叫,叫陈什么木。我去隔壁查一下,贫困户档案里有他们的名字。” 小武说着转身出了门,我只好又跟着他到了另一间屋子。这间屋和刚才那间卫生室完全不一样。刚才那间屋子里有一柜的药瓶瓶和一张窄窄小小的床,这间屋子的两张桌子和一排柜子都堆满了方方的塑料盒子和厚厚的纸袋子。小武站在柜子前,对着立起的塑料盒一排排看去,从其中的一层抽出一个。 “这是你家的档案。” 他打开这个塑料盒子,拿起里面的小册子和纸片翻了起来。 “哈,你叫‘陈又木’。晓得不?你叫陈又木。你爸爸叫‘陈贵群’,你妈妈叫,叫‘陈贵群妻’,呃,你妈妈没有名字?哦,你爸爸说过,你妈妈自己都不知道她自己的名字。嗯,你弟弟,你弟弟叫‘陈又林’。你要记住,你叫陈又木。别人喊‘陈又木’的时候,你就要点头或者嗯一声。” 小武看着捏着空饼干袋子的我,试着叫了声: “陈又木。” “嗯——” 我朝他点了点头。 “嘿,这就对了嘛。你还听得明白我说的话,我和你说话比和其他乡亲说话还省事。” 小武一边高兴地收盒子,一边对我说: “去,到卫生室隔壁的那个房子去,那个房子是乡上的文化室,里面有电视,你还可以在那儿看电视耍。” 桌子上的一个东西嘀嘀嘀嘀地响了。小武抓起上面一根藤蔓牵着的丝瓜般的东西,对着它像打手机一样说起来。我把吃空了的饼干袋放在桌子上,退出去找那间有电视的房子了。 卫生室和小武在的那间房子并排着隔了一个过道,我刚才跟着小武来时都没注意。这会儿,我独自穿过过道,又到了卫生室,门留着一个缝,不知何医生还在不在里面。我径直走到卫生室隔壁,这间敞着门的屋子就是有电视的文化室吗?我在门口停下,扶着门框朝里面望了望。里面没有人,也不见瘫子家中那种方头方脑的家伙,只见一块薄薄扁扁的方板子挂在一面墙的中间,黑黑的,什么动静也没有。 这是电视吗?里面怎么没有猫和老鼠,也没有人和其他会动的东西?我站在这块方板板面前,盯着它看了又看,只觉得亮锃锃的它更像一面黑镜子。在这面黑镜子里,我又看到了我自己。 我的头发长长了,毛糙糙的,显得更加篷乱,我的脸更小了,嘴巴和牙瓣更大了,晃眼一瞟,我觉得我越来越像一个人。我把背佝着些,这样,我几乎完全就是那个人了。站在这块黑镜子面前,我的心情突然沮丧到了极点。我多么不想像她,更不想成为她——在这个世界上,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她还知道什么! 我厌倦了这块可以照出人影的黑镜子,也厌倦了这块黑镜子照出的我自己。黑镜子旁边的两个架子很快又把我吸引了去。这两个架子不算高,每个架子从上到下有好几层,最高那层,我举起手也能够着。架子的每一层都插着些大大小小、薄薄厚厚的册子。花花绿绿的底色上,显着各种各样的字,这么多的字一下站在我面前,让我一时有些恍惚。它们好像都睁着眼睛在看我,在这么多眼睛面前,我突然觉得自己孤独无助,唉,要是瘫子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在这些字中,寻找着自己能认识的,就像在满山花儿中,寻找我熟悉的蒲公英和狗尾巴草。终于,我看到一个“大”字,这个字我认识,瘫子给我说过,一个人长大了,肩膀上可以挑根扁担了,就是大人的“大”。 找到“大”字。我似乎有了一点信心和底气,我又接着在眼前这片字的群体中继续寻找我似曾相识的面孔。“口”!我又找到了一个认识的,瘫子说大大方方一个口。“中”!口中穿一竖是中间的中…… 我正找得起劲,小武过来了。 “陈又木,你在干什么?那些是书,农村书屋的书,你看不懂的。哦,电视都忘了给你开,来,我把它打开,给你看少儿频道。” 原来,那块黑镜子就是这间屋子里的电视。这一天,我也不知道盯着它看了多久。也就在这一天,我才知道,电视里不只是有动画片,还有无数个世界。天空有天空的世界,海洋有海洋的世界,天空和海洋有合为一体的世界。幻想有幻想的世界,真实有真实的世界,幻想和真实有相互交融的世界。黑镜子好像一个魔幻的窗口,不断让我的眼睛和内心遭逢种种接踵而至的缤纷与奇妙。它乐此不疲地为我更迭一幅又一幅我想都想象不到的景象,这些景象往往连贯成一个个故事,故事里的男女老少甚至日月风雨、花鸟虫鱼……全然不避生疏地在我眼前欢欣着、忧愁着、讲述着,它们完全把我当作了一个对它们满怀兴趣并且真正能够理解它们的聪明的人。 在这个奇幻的窗口前,我也不知站了多久,直到这间房子真正的窗户外已麻麻黑,我才想起该回家了。我走出去的时候,电视里的人还在唱歌。我恋恋不舍地回了几次头,最后一眼,我在电视反射出的光的映照下,看见这间房子的门板上贴着三个字,它们是“文化室”吗?我想起小武带我来的时候说过这间屋子是乡上的文化室。 16.灯光 卫生室早关了门,过道对面小武查找我名字的那间屋子也关了门。小武呢?他把我忘了?还好,我看到过道尽头最后那间很大的屋子还透着明亮的灯光。我轻轻走过去,挨着半掩的门,往里一望—— 天啦,这间屋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们坐在围成一圏的桌子旁,每人面前都摆着一摞摞纸。他们一边埋头整理着,一边相互小声地说着什么。呃?那不是大个子叔叔吗?他怎么会在这儿?接着我又发现了黄支书、刘村儿、小武,还有“白围巾”!“银帽子”! 不过,除了他们几个,其他的全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人。他们都是从省里来的吗? 看着围坐成一圈的他们,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往衣服包里摸了摸。还在,“白围巾”送我的笔还在。但是,他们这些省里来的人怎么现在还在这儿呢?他们这样满满地坐一屋,是要干什么? “嗯,同志们,今天很抱歉,我们返回县城的小客车出了点问题,正在抢修,预计还有一个多小时能修好。现在七点过一刻,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就把原计划今晚回到县城才开的碰头会,放在村上开。这个会放在村上开也好,我们正好邀请黄支书、刘村长、小武书记和才从县里学习回来的村委会副主任岳主任一起参加。今天我们29督导组的各位同志对万顺乡苕花村贫困户的抽样调查走访,有什么还没有掌握清楚的情况,借此机会,可以再向几位村干部请教。黄支书、刘村长、小武书记、岳主任,辛苦你们了,我们知道你们在第一线工作很不容易,今天这么晚,耽误你们休息了,不好意思哈!” 说话的是斜对着我的一个瘦瘦的女人,她那么瘦,声音却很响亮,我看见她一说话,大家都安静下来了。 “莫得啥子喔,莫得啥子。” 黄支书清清嗓子说:“我们晚上开会也是家常便饭。白加黑,五加二,都是常态了。只是今天实在对不住靳书记、魏主席和在座的各位,今天你们分五个小组跑了一整天,现在都还莫有歇下来。村上条件有限,还请大家多谅解!” “关上门,就是一家人。大家都不说这些,为了抓紧时间,我看我们还是直奔主题。这样,在我们五个小组的十五个同志分别交流汇报今天的走访情况之前,我们首先请苕花村的村干部针对苕花村脱贫攻坚的总体情况给大家做个简要介绍。看你们几位负责人,哪个来?” 瘦瘦的女人微笑着看向黄支书、刘村长、小武和小武旁边那个可能是岳主任的人。 “要脱稿讲哈。我们到县上,县上的领导汇报扶贫工作,我们都要求他们‘脱贫攻坚脱稿讲’。能不能脱稿讲,我们就知道这个领导平常是不是真的把脱贫攻坚的工作抓在了手上,放在了心上。” “岳主任,你来。” “刘村儿,你来喔。” “小武书记,你是省上下来的,文化高,你来说。” “不,不,不……” 小武像我最开始学话时,连说了几个“不”。 “那这样,还是我来。我这张老脸,反正皮子厚。” 黄支书看他们几个都在推辞,干脆主动说道: “各位领导,你们看到的,在我们苕花村脱贫攻坚的工作中,小武书记、刘村儿、岳主任主要抓产业扶贫,抓项目落实,抓增效增收。另外,电脑呀网络啊,上传资料、建立数据库、报送信息基本上都靠小武书记,现在他又发挥专业特长,带领大家修村上的硬化路,他们几个都属于实干型,做得多说得少。我嘞,平常最多也就是卖点嘴巴劲,现在我就代表我们苕花村的村支两委做这个汇报。既然靳书记要求脱稿讲,我也就不照到材料念,全凭口头说,说得不全的地方,请小武书记、刘村儿和岳主任补充。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苕花村距万顺乡3.6公里,幅员面积6.85平方公里,地形以深丘山地为主,平均海拔多米,全村以传统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苕花村共6个村民小组,全村有户人,年被精准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年实现脱贫63户人,年实现脱贫55户人,年计划实现脱贫41户人,年计划实现脱贫24户71人,力争在年前,贫困户一个不少全部退出,实现贫困村彻底‘脱贫摘帽’。 “年以来,苕花村脱贫攻坚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组成了一支由县、省多家单位为成员的驻村工作组,工作组与村支‘两委’结合苕花村实际,动员全体村民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农业增效增收为核心,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不错,不错。黄支书,我看你把你们准备的材料都要一字不漏地背得下来了哈。” “嘿,有啥子法?上面各种检查啷个多,经常翻来覆去地讲,也就把嘴皮子磨顺滑啩啦。” “黄支书,你也不用谦虚,听得出你们村支两委对苕花村的脱贫工作是心中有数的,对当前和下一步的目标任务也是明确的。苕花村的脱贫攻坚一步一个脚印,正在稳打稳扎地推进。接下来,我们五个小组的十五位同志,就挨个交流你们进村入户的走访情况和真实感受,还是像前两天一样,谈你们的所见所闻,谈各自的所感所悟。既要说成绩,也要说问题,还要说说对策或建议。请大家畅所欲言,嗯,我们今天发言的顺序倒起来,怎么样?从第五小组说起,孟组长,你先开个头……” “那好吧,”一个中年男人接着说,“我说得不全的,请我们小组的其他成员补充。我们第五小组今天是留在村上,负责查阅苕花村脱贫攻坚的规划计划制订、基础档案、政策措施落实和项目实施管理的有关资料,访谈基层工作人员,了解全村“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推进,乡村基础建设和集体经济的开展情况。通过调查和对比,我们发现苕花村这几项工作的成效比较好,他们靶向定位、精准‘建档立卡’的工作搞得特别扎实。入户摸底调查、申请评议、公告公示、信息录入、资料归档等工作都规范有序。按照‘驻村联农户、户户有干部’的要求,村干部、驻村干部与帮扶对象开展了定期、定点、定户、定人的‘四定’精准帮扶,建立健全了扶贫对象动态机制,他们又通过项目规划、资金扶持、产业发展,确保扶贫到户政策的落实,为实施分类扶贫,制订帮扶计划和措施,确定扶贫内容、方法、途径和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提供了依据……” “我补充一下我们五小组了解到的苕花村的基础建设情况。目前已经完成的有安全饮水工程,电力工程和一些通讯项目,包括移动基站建设和宽带建设。同时实施了电力农网改造,确保了村民用电安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道路通畅工程,也就是硬化村内路和联户路。村上第一书记和其他村干部能坚持战斗在一线,及时解决施工用地、质量监督、劳务用工、建材保障和安全管理等具体问题,保证了工程顺利推进。” “我说说苕花村的产业发展情况。这个村因地制宜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产业,没有盲目跟风,不像其他村大家都去种花椒,大家都去养鸡,到时候花椒和鸡的销售又成问题。他们瞅准了自己的特色产业,一是皂角,一是雷竹。这次来,我才了解到,皂角全身都是宝,是一种多用途、高效益的经济树种。苕花村的土壤、气候特别适宜皂角生长,只是村民之前对皂角没有这样的认识,任凭它自生自灭。后来国家农委的一个工作组来这儿调研时给他们指出了这条致富路,现在苕花村发展皂角产业主要就是收获皂角刺,用来提取抗癌成分。一亩皂角可产刺斤左右,一亩收益多元,丰产期达得到元左右,可以带动一百多户农户增收。村上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村一个失明多年的贫困户,不能外出打工,这么多年挣不到钱,现在有了这个皂角产业,他每天就坐在家里面剪皂角刺,一天可以剪五六斤,比那些眼睛好的人还剪得快,一斤挣十元,一天可以挣五六十元。 “雷竹是苕花村下一步准备推进的一个产业。说雷竹也许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吃火锅经常配备的一种笋子,它的需求量大,市场前景很好,苕花村下一步就想打造一个总面积亩的雷竹产业园。雷竹三产可达丰产期,主要收获竹笋,平均亩产雷竹笋斤左右,一亩收益元左右,可以带动一百多户农户增收。另外,村上的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还在发展魔芋、核桃、枇杷、柑橘等经果林,这样又能带动一批农户脱贫致富。我们的总体感觉就是,苕花村发展产业不跟风,抓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路,这一点很重要……” 第五小组大概说完了。 “很好,五小组交流得很好,”瘦瘦的女人又说话了,她看着大个子叔叔,“我们继续。邱组长,你们第四小组还是请你先带个头。” 大个子叔叔姓邱?他挺了挺背脊,声音依然温和地说: “这个村民风很淳朴,干群关系比较和谐。从我们入户调查的情况来看,没有发现贫困户错评、漏评、错退的现象。我们了解到这个村以培训促进就业,开展就业精准扶贫技能和劳务培训,让村民很受益,特别是有的贫困户家庭成员被安置到扶贫公益性岗位就业,这个措施立竿见影,一下就改变了贫困户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在核算贫困户家庭收入时,村上把有的项目投入比如小额信贷和产业扶持基金、预期收入都算成当年实际收入,还是存在算账脱贫的现象。针对这一点,我建议对贫困户的家庭收入,哪些核算哪些不核算,村干部和帮扶人一定要弄清楚计入家庭人均收入的有九类,不计入家庭人均收入的有十七类,明白了这个,对贫困户的收入核算才能准确。” 瘦瘦的女人一边用笔记录着,一边说: “好!既有点赞,又有建议。第四小组的其他成员,请接着说。” 轮到“白围巾”说话了。她用手压了压下巴前的围巾,好让自己的声音不受阻碍: 下面,我想从我们小组走访到的其中三个贫困户家庭的细小之处,说说自己来到苕花村的真实感受。 一是在刘进福家。刘进福就是村里人喊的刘万一,他前些年外出打工,在工地从脚手架上摔下,医生说如果活下来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不是植物人。结果他真的活下来,也真的不是植物人,成了那万分之一。我们到他家时,他正扶着一根固定好的横着的竹竿在练习走动。让我震惊的是他双手扶着的那根竹竿,这根竹竿的表面,也就是他的双手来来回回反复把持的地方,已经磨得像不锈钢钢管一样发亮。看着这根亮锃锃的竹竿,我一下看到了刘进福对厄运不屈服的那股无形而顽强的劲头。他最终能下地走动,与他从未放弃过的希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在这根发亮的竹竿上,我看到了一种力量。 对不起,我说的是非常微小的细节,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数据和概念,可不可以? “可以啊,很好,你能从细微处有所发现,这些更生动具体,继续哈。” 瘦瘦的女人鼓励着“白围巾”。“白围巾”继续说道: 我觉得刘进福的妻子也很了不起。她对自己差点成为植物人的老公,给予了竭尽所能的支撑。其实,我们看到他们一家时,他们家很平常。老婆在忙里忙外,老公还是在扶着竹竿练习走动。他们夫妻二人各自安宁地做着各自的事,彼此甚至都顾不上看向对方一眼。念初中的孩子放学回来,自己就在两根一高一矮的板凳上做起作业来……就是这样的稀松平常和安宁,更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内心。我们每个人所渴望的亲情中的不离不弃,我在他们家看到了。这是贫困户家庭内部,亲人与亲人之间的相互帮扶。 第二是在钟越强钟瘤子家。钟越强嘴巴毒,说话狠。我们督导组来到他家他也没给个好脸色。大家知道一个人嘴巴毒,是因为心里苦,我同样特别留意了他家的情况。钟越强的老父亲和老母亲都疾病缠身,两个老人最放心不下的是他们的孙子,钟正轩。这个孩子在镇上读高中,我们这次去并没有看到他。学校远,钟正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他爷爷说他们拖累了这个孩子,孩子每天中午在学校只有五毛钱吃午饭,只够买一个馒头。但就是每天中午只够买一个馒头吃的五毛钱,这个孩子也省下来了,在奶奶七十岁的时候,他给奶奶买了一条十元钱的项链。十元钱对很多人来说,不算什么,对一根项链来说,也是低到尘埃里的价格。但是听见爷爷说这番话的时候,我马上在心里做着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这道题一做出来,我的心突然被深深地触痛了。十元钱啊,意味着这个孩子有二十天没有吃午饭。二十天啊,一个念高三的孩子!离开他们家的时候,我反复掂量着这根用绝不低廉的代价换来的十元钱的项链。我又想起爷爷说到这条项链时,穿得很厚的奶奶指了指自己的脖子,意思是告诉我们,孙子买给她的项链她一直戴着。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这条项链,但是我想这条项链,如果从奶奶的颈窝掏出,该是多么暖和! 这条项链,让我在这个贫寒的家庭看到了他们祖孙几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和向往。 第三是陈贵群家。 “陈贵群家?” “白围巾”是在说我家吗?我的耳朵几乎都要竖起来了。 “陈贵群一家四口,他,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四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障。他这一家,毫不隐晦和夸张地说,是我们这次督导的所有贫困村中最困难的一户。陈贵群只有一只眼睛,做不得什么事,村上人都叫他陈独眼儿。他的妻子是他从垃圾堆旁边捡回来的,又哑又憨。受遗传的影响和偏僻、闭塞、缺少早期智力开发和医疗救助等客观事实的限制,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又哑又憨。因为自身残障和家庭能力的限制,两个孩子没能接受义务教育。 我们小组仔细查看了他家的住房,老旧、破朽,还有几处在漏雨,好在村上已经把他家列入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的范畴,估计他家很快就会迎来一个巨大的改观。但是今天趁这个机会,省上的领导和村上的主要负责人都在这儿,我想特别提请大家多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uyazaoa.com/zyzxt/7479.html
- 上一篇文章: 治病偏方性爱后不能做的6件事
- 下一篇文章: 中药辨识活血化瘀延胡索的简介功效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