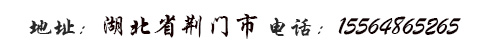马平我在夜里说话中篇小说专号
|
精彩导读 方圆左近的人已经知道,我又在夜里出门了。渐渐地,我就难得在那条路上碰到人了。人家躲我,我却不躲人家。从前我在夜里只怕跑得不快,现在,我不紧不慢地走着,一步也不虚。不管天有多黑,我都不会点着火把,或是提着马灯打着手电筒。这是我一直要走下去的一条路,我得把每一步都记下来,就是闭上眼睛也要一步不差到那儿。我在树根上坐下来,然后开始说话,有一声没一声。水莲喜欢听我说话,也喜欢我说话的样儿,所以,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多,睁开眼睛的时候少。我那个样儿,大概和说梦话差不多。但是,我对她说的大都是当天实打实的事。 我说,我不再跑着去下地了。 我说,我用盐水煮了花生,一个人吃就不香了。 我说,我已经把钱还给歪嘴了,还多还了十元。我没有说我借钱时受的那一场羞辱,也没有说我还钱时说的那几句话。 我说得最多的,还是麦穗。我说,我在夜里出门格外小心,我不能让他以为我又偷上了。我说,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夜里来这儿了。 ——马平《我在夜里说话》 一 我的小名叫麻狗。我已经五十七岁了,大名顶多被人叫过五十回。我的大名一般在关键的时候才用,就像我当年的新衣裳,要相亲的时候才穿。 这一次,我的大名上了报纸,还上了什么网,真是出了大名了。 我不能一上来就拣好事说,就说相亲,就说上报纸上网。我还是先说说我的身世。 我生在乡下,从小就没了爹妈。我爹在“大跃进”时得水肿病死了,这个你可能知道,“大办食堂”饿死的。不上一年,我妈又在堰塘里淹死了。夜里,我家的房子燃烧起来,村里的人听到呼救声赶去救火,却没有见到人影。天亮以后,才有人看见堰塘里漂浮着一只水桶,还有断成两截的扁担。我爹在世时那根扁担就断了,却被他用铁皮和钉子连接起来。我爹在扁担上做那个手脚,就是要让它在那火急的时候再断一次,好让我妈失去平衡,扑通一声跟他去。 那天夜里,我躲在生产队的花生地里,一声不吭睡到天亮。房子没救下来,我的舅舅找不到我的尸体,估摸着我妈已经把我丢到了屋外。一条麻狗把我的舅母领进了花生地。太阳已经出来,舅母看见我时,我正闭着眼睛咧着嘴笑。 当时我没满三岁,大概做什么好梦了。 我爹我妈就这样把我丢在了人世上。除了舅舅,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他只好收养了我。我从小就挨舅母的打,一直到我十八岁被她赶出家门。舅舅不打我,但他胆小怕事,从不敢阻拦舅母打我。我多吃了饭,我没让牛吃饱,我捡柴没把山背回来,我把尿屙到了床上,我把尿屙到了别人家的树根上,我起床迟了,我答应慢了,我把饭煮煳了,我平白无故把鞋穿在脚上,都要挨打。舅母用脚踢我,用巴掌扇我,主要是用很细的树条子抽我。 我有一个最大的毛病,一说话就紧紧闭上眼睛。所以,我挨打的时候是不哭的。我要是张开嘴巴哭起来,眼睛也会闭起来,树条子又是不长眼睛的,那就等于瞎子挨打了。 我不光挨舅母的打。后来,我成了一个小偷。你知道,小偷总会挨打。 我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还没有上学。 那天夜里,舅舅和舅母从生产队开会回来,我已经睡着了。我蜷缩在墙根的一堆红苕藤上,像一条狗。他们不落屋,我可不敢上床。他们点上煤油灯,就把我惊醒了。我听见舅母说:“看看,这个没人要的货!” 我赶紧站起来,又听见舅母说:“我想吃一根黄瓜。” 舅舅小声对我说:“你听见了?” 我说:“黄瓜还不能吃。” 舅母说:“我们家的黄瓜才起蒂蒂,我就该饿死,是不是?” 我明白了,舅母想吃别人家的黄瓜。我们家是一个单独的院子,却紧挨着好几家人的自留地,他们地里的黄瓜又粗又长。 “算了。”舅舅对舅母说,“忍一忍,天就亮了。” “算了?”舅母看着我,“能算了吗?” 我让舅母的表情打动了。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她看上去那样亲切,那样慈祥。我的瞌睡一下子没了。我溜出门,在院坝边上的老槐树下面停了停,然后向别人家的自留地走去。 满天的星星不停地眨着眼睛,我却是闭着眼睛摸到黄瓜的。黄瓜身上的颗粒刺了一下我的手,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 我还听见自己小声说:“黄瓜,跟我走!” 黄瓜似乎有点儿惊讶,还好,它们知道我可怜,没有硬拽着不肯下架。 我一手拿一根黄瓜,踩着满地星光往回走,真害怕老槐树突然咳嗽一声。 舅母把两根黄瓜都捋了过去。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连吃黄瓜的声音都没让我听见。 那以后,舅母在夜里对我说话,往往只有一句。 舅母说:“懒货,四季豆会来请你吗?” 舅母说:“好吃货,胡豆结在板凳上的?” 舅母说:“没用的货,白菜长脚了?它会自个儿跑到你家里来?” 舅母这样发话了,我就得出门去,把瓜果蔬菜带回家。 我上小学了。教室里没什么吃的,我就偷了一支粉笔回家。我还偷了一支铅笔,拿去讨好舅舅和舅母的独生女儿。我对她说:“姐姐,这是我在学校里捡的。” 姐姐也在上小学,比我高两个年级。她把铅笔丢在地上,说:“我不稀罕!” 我埋着头,不敢看她。 “路是各人走的!” 她这句话是从她的妈那儿捡来的。我不止一次听见她对她的妈说,不要让麻狗夜里出门了。她的妈也不止一次说,路是各人走的。 其实,姐姐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有一次,家里炖了一只鸡,天黑以后就要出锅了,舅母却催我出门了。我很卖力地抱了一个西瓜回家,鸡肉却已经吃光了,一口汤也没给我剩下。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泪水往肚子里咽。后半夜,姐姐悄悄到我的屋里来了。她不知用什么办法为我偷了几块鸡肉。 我有点儿想不通。她为我偷鸡肉,我为她偷铅笔,这有什么不同吗? 我只读了两年书,就不再上学了。我不是因为偷东西被学校赶了出来,而是让舅母拦在家里了。其实,我自己也不想读书了。读书要用嘴巴,而我一张开嘴巴就要闭上眼睛,书就没法读。天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嘴巴和眼睛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同学想看我的洋相,就逗我说话,然后把一片树叶一只蚂蚁一条虫喂进我的嘴里。老师根本就不叫我回答问题,所以我的大名在学校里也没有叫过几回。 我回家以后,却又有点儿想学校了。我拿出那支粉笔,在牛圈旁边的石头上写下了“打倒刘兰英”五个字。刘兰英就是我的舅母。我还没在课堂上学过这五个字,每一个字都是偷来的。那年头就兴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墙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打倒”两个字好偷。姐姐的课本上有一个女英雄,她的名字和舅母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我就偷看了姐姐的课本,偷来了“刘兰英”三个字。我写下这句口号以后,却害怕了。夜里,我悄悄溜到牛圈那儿,对着那石头撒了一泡尿。第二天一大早,我跑过去看了看,“打倒”还在,后面的字都可以认成“麻狗”了。 舅母她老人家可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今天,她都八十五岁了,一气吃两根黄瓜依旧没有问题。 没错,路是各人走的。我并不怨恨舅母,我不能说是她把我逼上那条路的。我不止一次梦见火烧我家房子那个夜晚,我是自己逃进花生地的。我爬得很慢,我知道大火追不上我。火光冲天,花生地很暖和。我醒过来后,嘴里总有花生的香味儿。我没满三岁就偷吃生产队的花生了,谁知道呢? 我的意思是说,我做梦都在做贼。 反过来,我做贼又像在做梦一样。 夜里,我溜出门做梦去了。我闭着眼睛,说着梦话。 我对茄子说:“懒货,跟我走!” 我对辣椒说:“好吃货,跟我走!” 我对西红柿说:“没用的货,跟我走!” 我这样说话,其实是在给自己壮胆。我在夜里出门,既怕碰见人,又怕撞见鬼。我从不敢到坟地附近去,那儿就是有猪肉我也不敢去拿。我连埋我爹妈的两个土堆都怕,就是在大白天也躲得远远的。 老话说,久走夜路会碰见鬼。我最怕的却是,走夜路碰见了人。 我不止一次被抓了现行。我还是个孩子,也没有人对我下狠脚狠手。尽管有人收养了我,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我是一个孤儿。我有吃百家饭的资格,何况舅母从没有让我吃过一顿饱饭。挨骂却是免不了的。骂人没好话,我爹我妈都被人骂过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我还要代人挨骂,就是一只狗不见了,人家也会骂到我的头上。要是骂我的人也有什么不好的名声,也让人看不起,我就会还嘴,甚至和他对骂。要是骂我的人有权有势,比如说是个干部,我只好一声不吭。 我被抓了现行或是把柄以后,舅母就会在人前打我。她这是要让人知道,我偷东西和她没有关系。她本来做做样儿就可以了,但她比平时打得还要凶。我也知道,她这是要让我长记性,或者多长个心眼儿。 我长记性了,也长心眼儿了,但我长不出翅膀,一有危险就扑棱棱飞走。一弯月亮挂在天上,我正在地里掏花生,几束火把突然围上来。火光亮得晃眼,我却瞎跑进了一片坟地,被一男一女按在坟头上。我当时大概吓傻了,好一阵才明白过来,他们把我的裤子脱了。我紧紧闭着眼睛,听见几个人和火把都在哗哗笑着。我还听见,我的裤子被抛到了一棵树上。火把熄了,几个人走了,我像小鬼一样从坟地里逃出来,却不能光着下半身回家。坟地边上的树有好几棵,每一团枝梢都像是我的裤子。我胡乱爬上一棵树,月亮却躲进了云里,再也不肯出来。我在树上摸索着,枝梢抽打着我的光屁股,却不肯把裤子还给我。我折断枝梢,丢到地上。我从树上下来,没有再上另外的树。我在那儿躺下来,用枝梢掩住下半身。坟地就在身旁,我用枝梢把脸也埋上了。地上隆起了枝梢的坟堆,我却不能像死人一样睡着。一条狗跑过或是一只鸟飞过,我都以为是鬼来了。我假装死了,迷迷糊糊睡了一觉,直到鸡叫声把我唤醒。天还没有大亮,我看见了挂在皂荚树上的裤子,两只裤脚在风中奔跑,就像在梦里一样轻飘飘的。我爬树的时候有点儿急,粗糙的树皮擦破了我的大腿。我在树上穿裤子的时候,差点儿掉了下去。 太阳出来了。我好像上了一趟天,刚刚回到地上。 那以后,我开始在夜里训练奔跑。我只要比别人跑得快,就等于生了翅膀。别人骂我有三只手,却不知道我又有了四只脚。我成了夜里的一股风。天上只有几颗星星,我跑过了两个生产队,正要对地里的魔芋下手,守夜的民兵突然冒了出来。我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民兵是专门训练过的,我都离家很近了,还有两个人紧跟在我屁股后面。我当然不能把他们领回家,就躲到了一棵老松树后面。我本来是要爬上老松树的,但两个民兵已经到了跟前,来不及了。 老松树比水桶还粗,我紧贴着树身一点一点挪着。民兵没有搜到我,骂骂咧咧走了。 我已经跑累了,在老松树的根上坐了一阵。月亮出来了,凉风也过来了。我索性在树下的草丛里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我梦见我已经死了,埋在那儿。我一觉睡到大天亮,原来并没有死。 我当然还不能死。我也得长大成人,讨一个老婆,和别人一样过日子。 就是说,我还是个半大孩子,就想着成家了。 一天夜里,天黑得像锅底,我摸到了一个南瓜。南瓜有点儿嫩,我都舍不得下重手。我轻言细语对它说:“小婆娘,跟我走!” 南瓜扭捏着,不肯离开它的藤。 我诳它说:“我把你领回家,让你做我的老婆……” 南瓜好像忍着,立即就要笑出声来。 我更来劲了:“你给我生十个儿子……” 南瓜扑哧一声笑了。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却不敢再往下说了。 南瓜又用女人的声音说话了:“麻狗,你也要偷人啊?” 我吓出了一身汗,睁开了眼睛。 月亮不知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看见了,南瓜旁边的草丛里躺着一个女人,她的身上还压着一个男人。 我的腿有点儿软,所以我没有跑远。树和石头好像都开口说话了,在给我壮胆。我不再害怕,又悄悄回到那儿。我不是惦记着那一个嫩南瓜,而是惦记着那一对狗男女。我趴在地上,听见那女人在不停地叫唤。我以为她很疼,却又听见她说:“使劲!你的牛劲到哪儿去了?使劲……” 他们完了事,却说到我了。 女人说:“麻狗那小贼货,别把我们的事说出去了。” 男人说:“他偷他的,我们偷我们的。” 女人说:“我们这不叫偷。” 男人问:“那叫什么?” 女人说:“我们这叫‘打平伙’!” “打平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简单地说就是平摊饭食,至少得一人出一道菜。他们都脱得光溜溜的,这等于说,他们一人出了一头脱了毛的肥猪。 我从地上抓起一把土,却没有朝他们撒过去。 他们没有发现我,穿上衣裳走了。我找到了那个嫩南瓜,搂着它睡了一会儿。嫩南瓜受了惊吓,就像个胆小的小女人一样。我没有脱光衣裳,所以,我和嫩南瓜不算“打平伙”。嫩南瓜却是光溜溜的,皮肤细腻极了。风吹过来,我怕它凉着了,就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没有把嫩南瓜带回家,我得让它养着。 那以后,我越来越喜欢在夜里出门了。 麦地在说悄悄话。 石头在喊叫。 稻草在呻吟…… 在苞谷地里,我听见男人对女人说:“你这身上啊,都没长骨头……” 在果园里,我听见女人对男人说:“你把我吃了吧,骨头都不要剩……” 这就让我犯糊涂了。女人身上,到底有没有骨头呢? 二 我把男人和女人的秘密偷回去,全都藏在床上了。我常常大半夜睡不着,恐怕已经让他们带坏了。 我并不是每天夜里都会出门。我窝在家里的时候,屁股就像扎了麦芒一样。野地里也并不是随时都有好听的故事在等着我,但是,我出去听听虫子叫,听听庄稼拔节的声音,也比在家里听舅母说话好。 我十八岁那年,天黑以后窝在家里,出事了。 那会儿是夏天,蚊虫的叫声就像地上过飞机一样。我想变成一只蚊虫,飞到姐姐的卧房里去。我知道姐姐正在洗澡。舅舅和舅母已经睡下了,我大概昏了头,把贼影子贴在了土墙上。我的一只眼睛在墙缝里看到了,木盆腾着蒸汽,灯光变成了水雾。姐姐背对着我,我只看到了一团模糊的白亮。 我正要换一只眼睛看,树条子落到了我的背上。舅母的嘴差点儿咬上了我的耳朵:“你怎么不去死!” 我从家里跑了出去,在老松树下面躲了一夜。姐姐要结婚了,却把我害成这样。那个要来倒插门的货嘴巴有点儿歪,他见到我时都不大愿意和我说话。他哪里知道,我对这个家的贡献有多大。那段日子,我成天想着姐姐的新婚之夜,想着她就要和那个歪嘴“打平伙”了,心里七上八下的,最后就忘记了她是我的姐姐。她其实是我的表姐,何况我并没有看到什么要紧的。我睡在草丛里,蚊虫叮着我身上的伤痕,我也懒得拍打。我想我真是一个浑蛋。 那个歪嘴,更是一个浑蛋。 我听见了舅舅的喊声:“麻狗!麻狗……” 麻狗这个小名,据说是舅母叫开的。我的爹妈最初给我取的那个小名,舅舅是知道的,但他也一直叫我麻狗。那条麻狗要是早知道我会坏了它的名声,大概不会把人带进花生地。我却并不领它的情。我就是饿死在花生地里,也比这样活着强一百倍。 是啊,我怎么不去死呢? 我从前睡在这儿梦见过自己死了,这一次,我却是真想了想死。人死了要是真能上天,就可以把这地上该看不该看的都给看了。但是,谁知道呢? 鸡叫二遍了,我打着空手回到家里。我怎么会想到,我已经被赶出家门了。舅舅大概一夜没睡,他让牛圈变成了我的新家。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变牛去吧!” 牛圈是独立的一间土墙房子,离老屋大约十丈远。牛得病死了,牛粪也已经下了地。一架木床,一口铁锅一只碗一双筷子,一把锄头一把镰刀,加上半年的口粮,这个家已经很像样了。我知道,这就算是分家了。那么,我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我在地上铺了一层泥土,把牛粪味儿压了压。我搬来三个石头支起了锅,然后自己动手砌了一个灶台。我还弄来一些旧报纸糊在墙上。牛圈原来没有门,我用树条子编了一道柴门。树条子是舅母打我的主要凶器,我用铁丝把它们捆绑起来,我想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我没有变牛,反倒是从牛变成了人。换句大话说,我要重新做人了。舅母管不着我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偷下去?我是一个社员,出工的时候格外卖力。我收工回来,没事就看一看墙上的报纸,找一找认得的字。 牛圈里缺一盏灯,我总不能摘几片树叶做一盏灯。天气越来越热,我常常在夜里爬上老槐树歇凉,从高处望着老屋。歪嘴已经来做上门女婿了,他和姐姐的卧房总是老早就熄了灯。姐姐让一个歪嘴拱上了,这让我比挨打还要难受。 我在大白天进了他们的卧房,把煤油灯拿走了。我是趁着没人的时候进去的,我觉得这不算偷。我从前的那间卧房里一直没有灯,大概没人想过我也需要一盏灯。我有了一盏灯,却发现它并没有用,灯光会在夜里把歪嘴招来。我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灯埋了。 歪嘴还是在夜里来了。他说:“你怎么不把灯点上!” “要灯干什么?”我问,“夜里有什么,需要点上灯看?” 歪嘴答不上来了。 我的眼睛不大争气,嘴巴却好使得很。我说:“你来了,我还用得着拿灯照着,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 “你过的这日子,点一盏灯,还真是一个笑话。” 歪嘴离开以后,我想想他这句话,差点儿把那灯从地下刨出来点上。 我已经习惯摸黑,事实上,我在夜里有点儿害怕亮光。有一次,我梦见地下的灯发了芽,长出了一盏大灯,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我惊醒过来,好一阵都没有弄明白,我是想一直这样黑下去,还是想要灯光照亮。 姐姐就像一盏晃眼的灯,我一见她就赶紧埋下头。我知道,尽管我一再让她伤心,她却是反对我住进牛圈的。我还知道,她已经在托人为我介绍对象了。 一个女人要是愿意嫁到一间牛圈里来,那么,她一定比一头母牛还要蠢。同样,我要是不愿意倒插门,我干脆就是一头牛。 姐姐对我说:“你给我把头抬起来!” 我抬起了头。我已经懂事了,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偷眼看她了。 我去相亲时少不了两件东西,一是要带上大名,二是要穿上新衣裳。我的大名一直像是偷来的,偶尔让人叫一回都像是被揭了短。我从记事起就没有穿过新衣裳,姐姐只得给我拿来一套歪嘴的新衣裳。尽管我讨厌那个货,但我还得打扮成他的模样,去走他倒插门那条路。 我和姐姐天不亮就出发,去二十里外的一个公社相亲。我的名声大概已经传到了三十里外,所以,我就是穿着新衣裳心里也在打鼓。我在场镇上见了女方一面,心里立即就踏实下来。我们生产队的姑娘没有那么丑的,我们大队也没有。我们公社可能有,但我没有见过。她要是早说不同意,我就不会请她上饭店吃一碗面。饭店里的人多得快要挤破脑袋,都像是刚从饿牢里放出来的。我刚把两碗面抢到手就被人挤开了。我这是第一次花钱买东西,两角钱却没有交出去。 那个丑姑娘并不知道这个,也不一定知道我更多的底细。我本来想对她亮一亮口才,但她不愿意和我说话,只和姐姐说了几句什么。 姐姐舍不得上饭店,一直饿着肚子。两角钱是她给我的,我本来想还给她,但我害怕引起她的误会。她的脸色不好,这就是说,那个丑姑娘没有看上我。 往回走的时候,姐姐对我说:“你那眼睛,该闭的时候不闭,该睁的时候不睁。” 我不该看她洗澡。她走在前面,我也不该看她好看的背影。 姐姐说:“人家嫌你的眼睛有问题。” 我没有说话。脚下是一段陡坎,我不敢闭上眼睛。 姐姐说:“你的眼睛和嘴巴是死对头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不能睁着眼睛说话。我觉得这不算什么问题,我的眼睛又没有瞎。事实上,我的手和脸才是死对头,我的手已经把我的脸丢光了。 我出了一趟远门,上了一次饭店,吃了一碗面条,还赚了两角钱。这可是我这辈子的第一笔钱,我把两张钞票塞进了墙缝里。我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分的粮食勉强能够糊口,但还没有分过一分钱。我在夜里把那两角钱从墙缝里抠出来,让它们陪我睡觉,天亮起床以后再把它们塞回墙缝里。墙缝多的是,那钱从没有在一个固定之处藏身,我却从没有记错。屋内不会起风,不会把钱吹走。屋外起风了,有时候会把钱吹到地上,但很容易找到。 我一共相过六次亲,每一次都要麻烦歪嘴的新衣裳,并且每一次都是奔着倒插门去的。总之,没有一个女人看上我。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并没有什么姿色,也没有把我打上眼。我想不通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生得并不丑,眼睛的毛病也算不上什么残疾。我承认我是一个贼,但是,比我名声更坏的贼都有老婆了。说到底,我还是太穷了。即便是倒插门,也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要一个从牛圈里出去的男人。 我爹我妈就是让穷害死的,我不能再穷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像样的日子,还得靠我的手。 我又在夜里出门了。我却像新手上路,有点儿害怕了…… …… ——摘自中篇小说《我在夜里说话》,作者马平,原发《四川文学》 阅读全文请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uyazaoa.com/zyzxt/8350.html
- 上一篇文章: 肩颈关节疼到不能忍中国制药百强药企放大招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